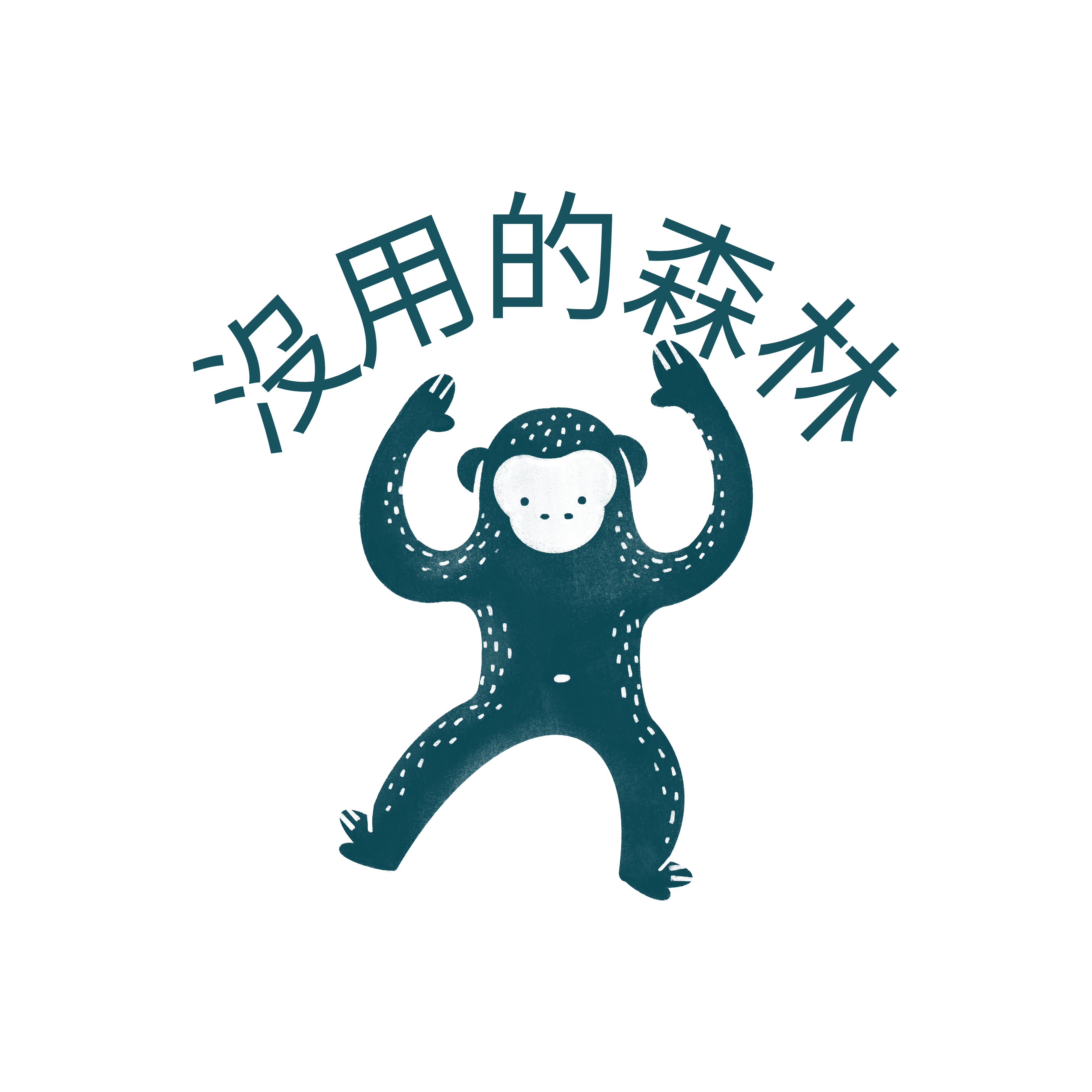知道我正在讀《攀樹人》,我的攀樹師朋友說,幸好我有攀樹的經驗。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即使現在,「攀樹」對多數人仍是未曾聽聞的活動。仰賴繩索、繩結、鉤環、吊帶、滑輪等工具攀升到樹上,和我們較能想像(而未必實踐過)的「爬樹」大不相同,包括我在內,剛開始攀樹的人最大的困惑和失落往往是:為什麼攀樹過程中幾乎不會碰觸到樹?
這個問題反映潛伏在每個攀樹者內心的慾望:我們攀樹,是為了和樹更靠近。
《攀樹人》的作者詹姆斯.艾爾德里德(James Aldred)同樣如此。即使他更為人所知的身分是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國家地理》頻道的生態攝影師,然而支持他足跡遍及婆羅洲、剛果、哥斯大黎加、委內瑞拉等熱帶雨林的內在動力,是對樹那難以言喻的熱情。
「樹木就是有某種令我著迷的地方,讓我一直回來,花時間與它們相處」,他寫道。在書籍出版後的一次訪談中,他用了一個比較抽象的說法:「我們無法定義樹。是樹在定義我們」。
我不懷疑這說法。當一個物種存在地球的時間遠超過人類,單一個體的年齡也以百年千年計;看似靜態,卻能以精算的體型結構應對各種氣候環境的變動,甚至能改變、創造出對自己有利的環境(一如艾爾德里德在書中提到的,雨林樹木能把水分蒸散到半空形成降雨)……要是人類謙卑一點,對樹木定義地球、生命、生態圈的歷史和能力,我們會深知自己連車尾燈都看不見。
但這本書多半時刻都沒打算跟讀者說教,要你愛護樹木、重視生態多樣、環保愛地球……沒有,它只是一本回憶錄,老老實實逐年推進,從十三歲因躲避急奔的馬匹匆忙爬上樹,獲得樹木的安全庇護,再到英國西南部的新森林初次攀上一棵名為「歌利亞」的紅杉;接著,為了到世界各地攀樹,詹姆斯成為一名生態攝影師,除了在沙漠、海洋捕捉生物景致,他和其他生態攝影師最大的差異,就是以熟練的攀樹技巧,將沉重的攝影器材背負到幾十公尺高的雨林樹冠層中,把超乎人類想像的動植物生活樣貌傳遞給坐在電視電腦螢幕前的我們。
當我的攀樹師朋友告訴我幸好我攀過樹時,我猜是因為詹姆斯在前幾章節對於攀樹器材、過程的細膩描寫,可能對未曾攀樹的讀者造成輕微的閱讀門檻:輔助將繩索拋上幾十公尺樹枝的「豆袋」是什麼?攀樹器具的使用順序、攀爬過程中人體對重力、對樹身的知覺經驗,沒親身試過似乎很難感受或理解。不過,一旦通過這些細節的鋪陳,詹姆斯平實沉穩的寫作風格所開展的世界,既有探險紀實的驚奇和趣味,也比生態節目中的影像多了更坦誠、深沉的思考反響。
當詹姆斯描述著婆羅洲雨林一棵四十五公尺高的絞殺榕樹上,一隻母黑猩猩忽然出現在他眼前,和他近距離緊密對望,隨後小猩猩也加入母親,甚至就在他面前放鬆睡著;在加彭的一棵硬鐵木上搭建拍攝用樹屋,卻遭遇蜂群的瘋狂襲擊,以及一隻有兩公尺象牙的憤怒公象連續幾日追蹤窺伺,攻擊蓄勢待發;在委內瑞拉拍攝猛禽角鴞如何在高四十三公尺的吉貝木棉築巢,卻因為靠近雛鳥而被重九公斤、展翅兩公尺的憤怒巨鳥在半空中抓得頭破血流……這些情節固然充斥濃厚的冒險意味,但詹姆斯說來不帶絲毫的征服口吻,而是更多戒慎和反思:人類記錄生態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入侵和干擾了生態,我們究竟該如何取得平衡?
畢竟,就算來到高處,獲取了俯瞰世界的權力,我們也只是這廣遼生態圈中一個再微小不過、和其他生命相同的生命。
我非常喜歡的章節,是詹姆斯記述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拍攝當地原住民科羅威人架設高空樹屋的回憶。幾乎從出生就會爬樹的科羅威人,樹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和崇拜對象,但為了在一棵合適的樹上造屋,他們可以毫不猶豫砍掉周圍一公頃林地。這種和樹木的關係對於習於文明價值的人自然是一大衝擊,詹姆斯不諱言自己感受複雜,但他把質問的矛頭對向自己:
「我對樹木的情感是不是只是一種對自身性靈需求的投射,只為填補正規宗教帶給現代人的不信任與空洞?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夠幸運,能再遇到科羅威人,一定要多問問他們對樹木的感受是什麼,如何在性靈層次上與樹木產生連結?雖然我知道,這好比是在問魚兒對水的感覺,或是問小鳥對自己翱翔的那片天空有什麼感受一樣。」
摘下這句子,是為了把問題也留給自己。於是一次次回到樹旁,我或將知道如何丈量樹木與我自己的生命。
※本文首次公開刊載於博客來OKAPI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