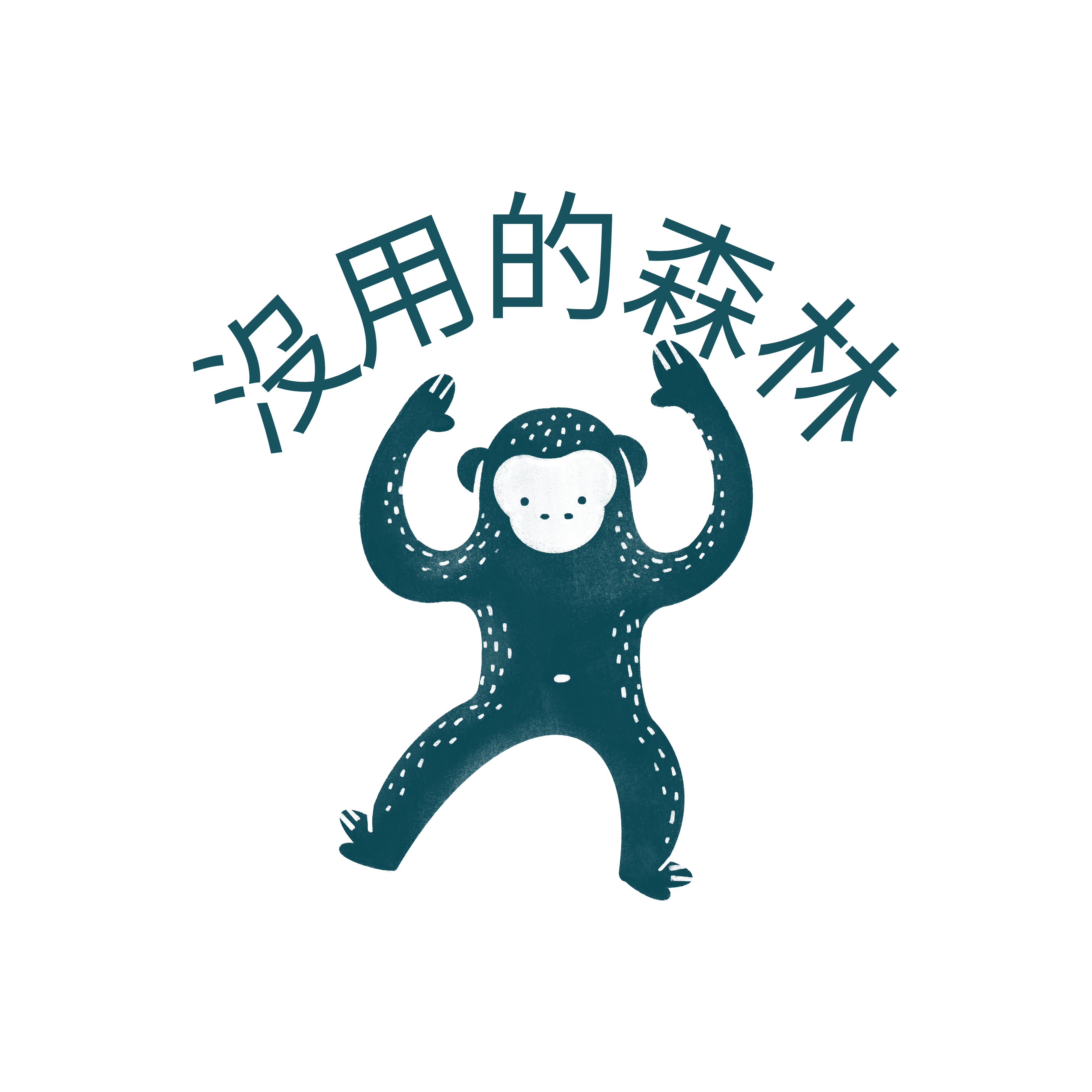穿過長長的雪山隧道,便是宜蘭。青空下一片綠油油,葛瑪蘭客運在轉運站前停了下來。
從這裡啟程前往福山植物園,還要40分鐘車程。但是,從台灣各地,乃至遠從中港澳星馬來的遊客,仍願意多花上這段時間,一睹這座深山中的植物園,何以成為台北植物園之外另一個富盛名的國家植物園——尤其,與位在市中心、親民開放的台北植物園相較,福山植物園不只地處偏遠,入園門檻還出了名的高。一位知名的郊山野遊部落客曾形容,福山是「一入侯門深似海」。
要入福山植物園的門,首先得在35天前上網申請入園許可。園內採人數總量管制,平日最多接納500人,假日多一點,600。入園不需費用,但是得遵守各項遊園守則:不帶寵物、不留垃圾、不吵鬧喧嘩……官網上近10條守則以「叮嚀」取代,記不起來沒關係,入園前要聽完才放行的志工解說會再次提醒。
一天接待500人,想必大型遊覽車滿載乘客而來也是有的,但福山的出入口只有一條窄窄的台7丁聯外道路,大型遊覽車上不來,滿載的乘客只能改搭9人座,從山腳浩浩蕩蕩,一路駛向海拔600公尺、橫跨新北烏來與宜蘭員山的深山植物園。
我初次上福山就曾見識這浩浩蕩蕩的景象。中午剛過,七、八台9人座客車在管制站前排成長長的縱列,等待管制人員核實入園者身分後陸續放行。這道程序增添了福山的神祕性,或許,也構成了另一種非到不可的吸引力。
但這次我們並不需接受耐心等候的考驗。再訪福山的這天是休園日,我們也非訪客,而是帶著採訪任務前來。「芝麻開門!」駕車接送我們的張淵順搖下車窗大喊,緊閉的管制鐵門應聲而開,他呵呵一笑,車過又一聲:「芝麻關門!」
在福山當園丁當了30年,這條台7丁,就算不說閉著眼睛也能開,對張淵順也差不多是這意思了。雨霧逐漸聚攏在前方馬路上,他像是安慰一樣開口:「這就是福山一般的天氣……這種天氣,動物出來的機會很高」,果然,車子一拐彎,一隻猴子赫然坐在馬路護欄上。我們發出驚喜的呼聲,張淵順波瀾不驚,「牠們搞不清楚為什麼天亮了這麼久,太陽還不出來。要是太陽大,牠們就躲起來了」。
他說起在這條路上的各種「蒙難記」。騎摩托車被撞過、開車也被撞過,肇事者多是山羌和長鬃山羊,人們駕車經過時,牠們會猛地從暗處竄出,迎頭撞上來。有一晚,張淵順開小貨車下山,一隻長鬃山羊在馬路中間,尊臀朝車,兀立不動,他閃燈示意,沒想到山羊怒了,以羊蹄不住踱地,接著直直撞向貨車,張淵順只好輕觸喇叭,這個蠻橫的肇事者才躍過護欄,消失在邊坡另一頭。
「牠們都肇事逃逸啦!」那次車子被撞出一個窟窿,但張淵順也只是大笑。後來我們會知道,這條路上的漫遊者所在多有,福山的工作人員早已習慣慢速行車,以免驚嚇碰撞到這群不算意外的嬌客。
嬌客不只出沒在台7丁沿途,事實上,整座福山植物園就是牠們的家。拜訪過福山的遊人們,總會津津樂道在園內親眼目睹過多少動物:山羌是基本必備款,這種台灣最小的鹿科動物素以膽小聞名,在福山卻擔當起迎賓使者,在距離人類五公尺處悠悠哉哉上演啃草秀。
看到山羌不稀奇,和獼猴家族相遇也不意外,長鬃山羊願意賞臉,你才有資格炫耀自己的福山經驗。曾任福山植物園管理員的林建融說,目前園內有三隻長鬃山羊出沒,能看到一隻就算相當幸運。那麼,就容我炫耀吧——到福山拜訪的這天,我們三隻都見到了。
除了這幾類體型較大的動物,來到福山的遊客們也樂衷於尋找食蟹獴、麝香貓、穿山甲、台灣葉鼻蝠、大赤鼯鼠、藍腹鷴等空中和陸上動物的蹤影。我想起2018年夏天,因為參加一個生態一日旅遊團而初次拜訪福山植物園,9人座客車中有幾位回頭客,都是為了野生動物而來,他們興致勃勃地數著看見長鬃山羊幾次、藍腹鷴幾次、食蟹獴幾次……其中一位退休大姊甚至被譽為吉祥物,只要有她在,當天必定遇到難得一見的動物。
「我都說我們這裡是『福山動物園』啊!」原本負責植物維管、現在專職瀕危植物保種的林建融說著,聽來有一絲埋怨。他看著衝向前對一群獼猴家族不住拍攝的攝影師,「今天第一次看他按這麼多快門……」

自由自在徜徉於山林之中的動物,成了福山植物園吸引遊客前來的主要號召,人們說,福山得天獨厚。或許正是這份得天獨厚,讓泰雅人數百年前便循著貫串福山的哈盆溪流域建起聚落和獵場,也讓前來殖民的日人發現這片北台灣闊葉森林涵養水源的珍貴潛力,保留了森林原始風貌,沒讓伐木的巨斧長驅直入;在國民政府管轄後,這片山林成了國有林班地,而後在保育呼聲漸起的1990年代,逐漸成為自然環境研究、保護與教育的示範區域。
不過,在林建融眼中,福山的野生動物之所以能悠遊園區內而不畏人,「是自然教育成功,不是得天獨厚」,畢竟,動物生活在自然中,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要不是有外敵或危機,何須特意隱匿自己?30年的解說教育,讓遊客懂得尊重動物,動物才願意跟人類保持這恰到好處的親近。
但自然教育並非福山植物園開設的初衷。福山植物園的正確名稱是「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這個隸屬於國家林業機構下的單位,主要任務是學術研究與產業試驗。1990年,當這個擁有1000多公頃林地的研究機構掛牌成立,很快引起外界矚目,要求開放的聲浪不斷湧現,迫於這份壓力,福山研究中心劃出了20多公頃包括人工水生池、植物標本園在內的區域,以「福山植物園」的名義在1991年元旦當天對外開放。
首次開放的結果,可用「慘烈」形容。新聞釋出消息後,源源不絕的人潮趁著連續假期湧入園區,撐了三天,植物園匆匆宣布關園。當時任職首任分局長的夏禹九描述,「開放三天,福山的連外道路天天塞車,植物園區到處都是垃圾,簡直是一場災難」。(註:上述歷史見〈福山植物園自然教育推展的歷程及願景〉,《與植物園一起變更好!台北植物園120週年紀念文集》,2016。)
植物園到底該不該開放?長時間的全盤檢討和規劃後,1993年12月,福山植物園重新對外開幕,從金門來台念書的黎明儀,當時剛從屏東畢業,在福山工作的學長一句「來當解說員」的召喚下,連解說員是什麼都搞不清的她,就這樣誤打誤撞進了福山,成為最早的兩名專職解說員之一。如今,黎明儀是福山自然教育推廣的幕後推手,官網上設計親民可愛的一系列「認識福山」主題學習單、介紹福山森林和大型猛禽林鵰的紀錄片、自然種子教師研習,以及園區入口作為遊客教育前哨站的「自然中心」,都有她的規劃和參與。
福山的自然解說,從早年介紹台灣的林業發展、植物知識,到近期著重森林生態與環境教育,大致循著時勢潮流和機構轉型而演進。一開始,擅長做研究、搞學術的科學家們,對於如何解說、怎樣推廣都摸不著頭緒,黎明儀等人摸索許久,找到一條最簡單樸素的路:如果想讓遊客為眼前見到的自然景物開心,覺得自然環境很好,進而想愛護、珍惜它,那麼,要和他們說什麼?
答案恐怕不是動植物的學名和抽象的生態概念,而是讓遊客知道:
人類在這裡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在此生活的其他生物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既然我們是過客,牠們才是以此為家的主人,對所有生命抱持尊重、自律的態度,是進入這片山林,乃至於所有自然環境的人類基本守則。
所以,福山沒有垃圾桶,是為了避免動物翻找取食,改變覓食習慣;不得餵食野生動物,才能保留動物與人類的美好距離,也避免發生動物搶食、攻擊人類的情況。
入園時間避開清晨和傍晚,因為那是動物們出來覓食行動的時間;人數總量限制,才能盡可能降低人類活動對生物的干擾,減少環境壓力。擾動環境生態的,不一定都是颱風這麼激烈的發生,更多時候是微小的蝴蝶效應。好比一隻跑進園區、神出鬼沒的流浪貓,就足以造成所有鳥類的恐慌,又或是宗教信徒宣稱良善的放生活動,讓成千上百條眼鏡蛇沿著台7丁和園區出沒,但很快地,因為不適應環境,所有的眼鏡蛇都消失了。(註2:2012年6月,有宗教信徒在福山植物園、雙連埤附近山區大量野放保育類的眼鏡蛇等蛇類,但眼鏡蛇棲地主要是低海拔高溫區域,除涉嫌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外,保育人士也認為此舉不僅破壞生態平衡,也形同殺生。)
「有時候,我們做很多不適當的事情,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整個生態系是怎麼運作的,如果沒有過度干擾破壞,生態系就能運作得很順利,當它運作正常,人類也能從中得到好處」。站在一座木橋上,黎明儀指著橋下清澈的哈盆溪和兩岸狂放茂密的蕨與樹,「這裡樹木覆蓋地非常完整,所以保護能力很強」,就算颱風來也少有邊坡崩塌,也因此,不對外開放的水源保護區才能永續維持最佳水質,提供大台北居民的生活用水。
說到人類戒慎恐懼的颱風,是福山植物園重要且必須的年度訪客。森林是亟需毀滅與重生交替循環的生態系,「有些森林是靠火災,我們靠颱風」,要是一整年都沒颱風,「我們就會擔心,例如虎頭蜂會變多,水會不夠,著生植物的生長也比較差,或是昆蟲很多、把葉子吃光……可是颱風來幾次,森林很快就能恢復正常功能,也減少很多經營管理的力氣」。
「哈盆溪真的很強」,林建融從旁附和,颱風來時,「一般河流都是黃沙滾滾,但它就是保持清澈,完全不會濁,只是水位變高」。枯水期的時候,他會沿著溪谷溯行,檢視沿途植被。走在人們形容為「台灣亞馬遜」的地景裡,能形容那經驗的字眼,他說就是,美啊。
從林業展示到今天的生態保育,福山植物園用這片低度人工的山林所揭櫫的,是名為「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的關係。若說傳統倫理學是一種道德的尺度,界定人與人相處的分際,那麼自然哲學家羅斯頓(Holmes Rolston)等人倡議已半世紀的環境倫理,就是在意識到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造成的毀滅性浩劫後,企圖補救的一系列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辨。
倫理二字聽來有些道學或沉重,然所有掛上「倫理」的觀念,本質的探問幾乎都是:
身為人,你願意多尊重共處的對象?能為這個對象生存的權利做到多少自我節制?無論他是人類、動物、植物,或充滿更多不可見生命的生態系?
這些以倫理為名的問題,就經常在林建融的腦中無限分枝蔓延,尤其是,當他開始主導福山植物園的「方舟計畫」後。
方舟計畫是林試所自2019年開始執行的一次大型專案,以四年為期,由台北植物園主掌,其他五所國家植物園和數個民間機構合作,目標是將《2017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裡羅列的989種國家受威脅野生維管束植物,盡可能做到移地保育。
談到保育,一般人或許知道原地保育,以維護整個生態的永續生存,移地保育卻不然,有時是原棲地有消失之虞,有時迫於環境變異或人為採摘等因素,導致植物族群瀕臨滅絕,這時植物學家便把面臨生存危機的植物攜回植物園保存並繁殖,為它們留住下一代生機。
雖說初衷良善,但一直以來林試所的移地保育舉措屢受質疑。生態學泰斗認為光是採摘植物做移地保育,無法留住整個生態系以維持生物多樣性,就算不上復育;民間人士則質疑:為什麼公部門扛著「保育」大旗就能大肆採摘瀕危植物,一般人就不能動手採回家復育?而瀕危植物數量已經很低,誰知道原棲地的族群會不會因植物學家採集而更快滅絕?
「這是必要之惡」,林建融坦率說。事實上,打從福山植物園設置以來,蒐集台灣各地原生種植物放進園區,等於把外來種引入,風險本就存在,但是,植物園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物種,兩難權衡下,引種保育還是得做,用提升植物園的公益性價值來彌補生態承擔的風險。
至於植物研究者採集植物,更是不得不為的「惡行」。目前,方舟計畫各單位出外採集,會遵照分區原則或交流資訊,避免同一區域的植株被重複採集。林建融也認為大眾不應苛責為研究而做的採集,畢竟「要是分類學家沒發現這個物種、幫物種留下證據,我們做保育的根本不知道有對象要出手」。
出手或不出手,對採集者來說,舉手之勞底下,有時承載千鈞重鼎的壓力——壓力的名字是「採集倫理」。比方,所有採集的人都知道的基本倫理:不採你所見的第一棵植物,因為你還不知道族群總量有多少,萬一它僅此一棵呢?

不只第一棵採不得,最後一棵該採?不該採?這也是保育界爭議的大哉問。「下手之後,它就野外滅絕了,不下手,它滅絕就是滅絕」,差別在於,被救走的最後一棵可能在實驗室裡繁殖出更多。近期台灣就有兩株「最後一棵」,在保育界決定不出手後,迎向截然不同的命運:野小百合的最後一棵野生植株沒結果,但研究者剝下一片鱗片回實驗室做無性繁殖,最後培育出數百株。蘭嶼茜木就沒那麼幸運了,林試所另一位研究員鐘詩文曾在蘭嶼見過的最後一棵,如今已消失無蹤。「茜木就卡在一個,不夠漂亮」,林建融惋惜說,「我們對茜木了解得不夠,應該想盡辦法把它留下來的」。
除了第一與最後,面對一群瀕危植株,多少數量可取回多少比例?要取整株還是只拿枝條?就連要採看來漂亮的還是醜的,採集者心中有無數考量、無數抉擇:「尺全在自己心裡耶!沒有SOP可以把這個講到鉅細靡遺」,林建融說,但最終總有一把尺幫自己做出最後判斷,那就是:
「我是愛植物的。要讓這植物不論在我的溫室或原棲地,都可以活下去」。
這個一定幫植物活下去的信念,令他也坦然面對「移地保育不算保育」的質疑:「我們都說預防重於治療,但問題發生了難道就不治療嗎?移地保育和原地保育並沒有衝突,只是多加一個確保」,更何況,即使採走植物,林建融仍不時回原棲地探望植群,但棲地的消失總是快得教人措手不及,就算大發宏願買下所有棲地好了,土地的產權、管理權都不同,取得權利曠日廢時不說,只怕成功那天,植物們早已不存在。
沒能救到的植物、消失過快的棲地,讓為了尋覓植物上山下海、連墓仔埔(台語「墳墓」)也敢去的林建融一度消極抗拒,特別是水生植物,「有陣子我非常排斥收水生植物,因為收集過程的心理打擊很大,消失速度實在太快,可能你才知道一個新的棲地,結果去的時候它已經徹底消失了」。
水生植物消失的速度到底有多快?福山植物園下方的雙連埤,恰有一段植物消亡的進行式。這個滿布埤塘的山坳,曾因多達三分之一的台灣原生水生植物在此繁衍,被譽為「水草王國」,然而90年代後持續進入的外來者,成為慣行農作之外一股加速棲地生態滅絕的強大力量。
曾在雙連埤租地種菜的張淵順,就曾親賭外人買地「種房子」如何造成水生植物滅絕的場景:他種菜的地被地主賣給了想蓋農舍的台北人,新地主發現地上還有一片小溼地,就買了一堆草魚放進野生水域。草魚來了,水草就遭殃了,小巧可愛、據說很可口的食蟲植物黃花貍藻首當其衝,「我發現一兩年後,就沒有那個可以撈了,都被吃光了」。
「最恐怖的是這些外來種魚類是無法移除的。整個雙連埤那麼大,要怎麼撈魚?怎樣都撈不乾淨」,林建融說,不只草魚肆虐,慣行耕作的田地與植物棲地經常重疊,福壽螺、除草劑、外來種植物也就堂而皇之入侵。
在一個旁邊種滿蔬菜的雙連埤小水渠裡,林建融蹲下身仔細翻找,好不容易翻出一小簇嬌嫩鮮綠的植群,「這是桃園石龍尾。疑似原生族群,但我們無法檢測它是人工種植還是原棲地的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個在2017年確認「野外滅絕」的水生植物悲傷的命運終曲似乎得以翻轉,但林建融很快澆熄我們為它振奮的心情,「你看,旁邊的粉綠狐尾藻長得很快,這是強勢外來種,很快就會佔滿這裡。」
到時候桃園石龍尾可還有棲身之處?林建融搖搖頭,「很難」。
至少,早先移進福山植物園裡保種的桃園石龍尾,有個相較之下可說幸福快樂的際遇。桃園石龍尾是方舟計畫第一波曝光的「明星保種植物」,除了野外滅絕的悲慘身世外,或許也因為它在水中亭亭玉立的模樣實在太討喜。
亭亭玉立的文學修辭,換了科學家語言就是「挺水葉」。桃園石龍尾的葉子有兩種形態,挺水葉顧名思義是挺直於水面上,沉水葉則在水中不強出頭,挺水開花而不結果,沉水則無花果。一開始,林建融對怎麼種桃園石龍尾頗棘手,不是種不活,就是全都不開花的沉水葉型。有一天,他無意中把一些沉水的石龍尾勾到竹筏上,沒想到離水後的桃園石龍尾,在竹筏上自顧自長成了挺水葉型態。
林建融從中體會出一個道理:過去他們栽培移地保育的植物時,都強調「要模仿原棲地」種植,也就是遵循已知條件,但「這概念是錯的」,他舉例,植物剛採回來時根系受損,需要比原棲地更好的條件,而新環境從介質(土壤)、溫度、降雨、海拔……和原棲地往往不同,不可能用一模一樣的條件栽種。這個例子更具科學意義的地方在於:植物的型態和生長仍存在許多未知,要探尋發現,除了偶然與巧合,更需要跳脫既定框架的思考。
跳脫框架有很多方法,以負責栽種的園丁來說,從做中學最能跳脫照本宣科,尤其,許多移地保育的植物過去鮮有相關研究,當這些陌生且種類繁多的物種進入植物園苗圃,對園丁的考驗旋即接踵而來。過去,福山植物園作為林業研究中心,苗圃中多為林木或景觀作物,種類少而個體的數量多;現在苗圃裡的保種植物,每種的數量可能三、五棵,但物種量達到1,000種,從設備到照顧管理的方法,都和傳統育苗有很大的差異,「方舟計畫可能會是苗圃發展史的轉捩點」,林建融說。
身兼採集者和園丁的林建融,也以目前還在植物園工作的前任園丁張淵順為師,因為張淵順是綠手指中的綠手指,常常林建融試種失敗的植物,交到張淵順手上就能成功繁殖出一大堆。問張淵順為什麼手指能這麼「綠」,他笑笑說,就是注意小細節,好比野採回來的植物若沒馬上種植,很容易缺水萎掉,他為了幫裝在密封袋中的植物保水換空氣,硬是可以在周末假日天天開車上山,把植物的袋子一一打開,放空氣進去,再綁起。
張淵順和林建融也一再強調,植物園栽種這些保育植物,和民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們非常注重種源紀錄,哪一棵植物何時入園、繁殖到第幾代,自然授粉的情況下子代表現如何……把野外的種源完整保留下來,將來有機會移回原棲地復育時,才能確保基因多樣性留存在野生族群內,而不像園藝栽種或一般人摘採回家種植,容易發生雜交或基因污染的問題。
在福山的兩天,看了不下數十種搭上方舟、重獲生機的瀕危植物,有的嬌美,有的其貌不揚,有些是上個世代台灣人的童年回憶,有些則仍存在於城市牆縫,只是未曾得人青睞。這些安靜的植物,也許不如園區的動物吸引人類眼球,卻是植物園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一位經常載客前來福山植物園的計程車司機山野人說,遊客多半是聽聞福山大名而來,但真正對植物有興趣的人,可能一百位客人當中只有一個。
在離開福山前,林建融和黎明儀帶著我們走進園區一處僻靜角落,撥開半人高的草叢後,面前赫然出現一面乾淨透澈的池沼,池子裡頭,滿是一度滅絕的桃園石龍尾。它們全都沉於水中,輕輕搖頭晃腦,似醒似睡。綠得非常濃艷。
「這是我們的祕密基地,今天首度公開」,林建融表情忍不住洩漏一絲得意,「不是刻意弄的,是某次氾濫淹水後自然形成一個水池,我們就把它作為桃園石龍尾的保種基地。很漂亮吧?」
那的確很美。想到並不很久以前,台灣隨處可見的埤塘水池裡盡是這樣的景致,眼前那過分鮮綠到幾乎不真實的桃園石龍尾,教我不由想起了博物館裡戴上VR裝置就可看見栩栩如生的史前生物,例如恐龍。
如果有一天,連這樣的祕密基地也不可得,是不是即使在福山這樣的植物園裡,我們也得戴上虛擬裝置,才能重新和消失的植物重遇?
(本文首次公開刊載於 端傳媒「台灣植物園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