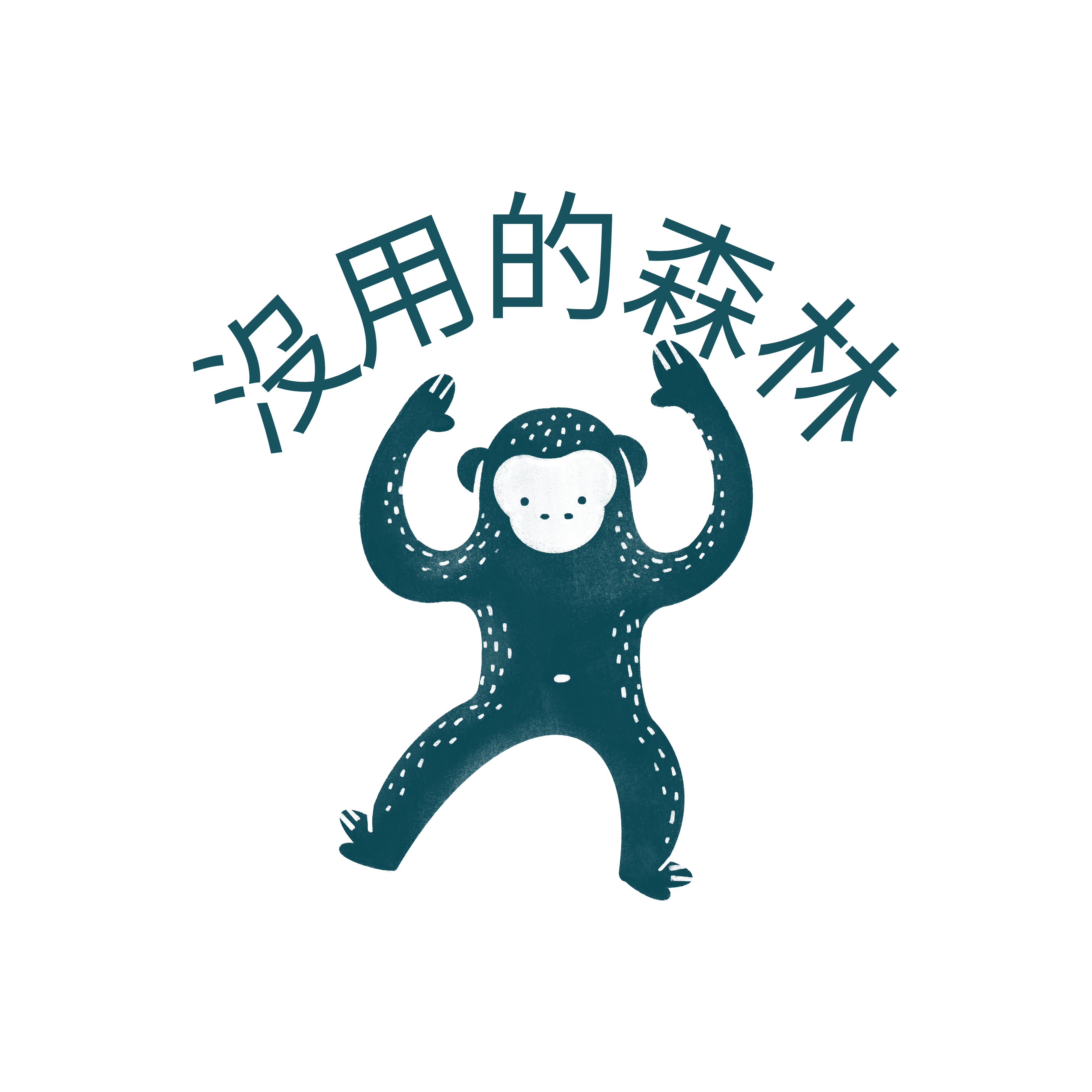說也奇怪,每年此時,我經常想起一首詩: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敲打文章這日,臉書的去年今日更直接跳出一張辛夷花照片……昨晚才想好要用王維這首〈辛夷花塢〉開篇,看著去年從網路上抓來的璀璨辛夷花苞,只能告訴自己,這恐怕不是什麼共時性,而是我體內自建的花季作怪。
我一直對後世解讀這首詩的主流說法頗有意見。論者多從王維的生平脈絡推測,當時從仕途歸隱田園的他仍心懷朝政,所以用山谷中盛放卻無人鑑賞的辛夷來自況。老實說,漢文化男性創作者老愛拿他者(從怨婦到植物)來自傷自憐,讀多了也真是助長玻璃心外加毀人美感力科學力。不過這裡我不打算罪責作者和論者,直接繞過他們就好——
用中(任)性的眼光來讀這首詩,能感覺到的,也就是辛夷花任性。管你要不要千里迢迢冒著車流迴堵的風險來進行一個賞花的動作,甚至不管你們訂下的什麼四季節氣,我們植物可是繞過人類定義,直接跟環境所有存在打交道的。你們說是氣候變遷,在我們,就是感知到了應當或不應開花的徵候,跟著做出回應,盡可能爭取繁衍或蓄積生命力的最大可能。
如果覺得辛夷花的美太遙遠導致你無從發作想像力,不妨想想前陣子花期剛告段落的山中桐花吧。遊人們一頭鑽進山徑中,對著覆滿整片山徑的雪白桐花打卡按讚不說,還得撿起來排愛心或串花環。滑著這些臉書IG照片時,我想起的是某條我騎車漫遊經過的山路。一條陡峭的泥土路從鄉道上不意岔出,我停車駐足,目瞪口呆看著早已不是泥土路的一哩桐花布。我沒涉足,只是把它放進心眼,供日後長久凝視。一度有用的桐花,被植滿台灣中北部淺山,如今除審美和文創外幾乎無用,但我並不為此感傷。想到或許更多無人處桐花自開自落,與人間無涉,它完成了自我的生命而不需被鑑賞定奪挪用,不好嗎?
可是若與人間太過無涉,它們也可能無聲無息滅絕。我想起去年秋冬交接時去拜訪的福山植物園,負責到野外搜尋、採集瀕臨滅絕植物,將之移回植物園培育以達到保育保種的研究員林建融,帶著我進入苗圃,用手去指那些根本雜草一樣,連美醜好壞都說不上,而是更糟的——不入人眼而缺乏存在感的植物們:赤箭莎、克拉莎、異萼挖耳草、畢祿山苧麻……
雜草一樣,又不像昭和草、車前草、龍葵等「野菜型雜草」可食可用,連用手去指,看的人還會茫然四顧:「你說的那個什麼箭在哪裡?」它們是一群平淡的生命,平淡到你踩死了它們、毀掉它們的棲地、使它們一株也不剩地從地球上消失,都能一路無所察覺。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人要為它們疲於奔命,用力挽狂瀾的能量將它們帶回園裡保護、培育、延續生命。
這麼做是為了維持「生物多樣性」,這些人類說。我原本把生物多樣性簡化理解為「自然環境裡本有的生命缺一不可」,但發現生物多樣性希望保有的更微細:它不只要一個環境裡的生態系、物種種類和數量盡量豐富(且不過分偏重),還要每個個體的個別差異和內在變異性都保存下來。也就是說,你作為一株植物,我不只要保住你和你同類在此生存的權利,也要確保你跟你同類「同中有異」的部分能繼續(用植物學家的說法是「基因多樣性」)。於是,等到旱災、風災、蟲災、水災、病毒害……大難來時,你們的差異將造成某些死亡、某些倖存,那麼,你們這族群的集體生命終究可在地球上存續。
人類喜歡想像自己的生命獲得某種無窮延續,因此愛烏及屋。另一方面,人類也害怕自己生命無法延續是因摧毀太多其他物種生命,所以拿生物多樣性為說帖,試圖發給其他大舉摧殘生命的人類。我不確定這說法是否真能觸及那些一心(或根本無心)造成生物滅絕的人,但,當一個不忍見到任何植物滅絕的人在我面前說,不是因為植物有用或漂亮才要留它,而是所有的生命都有其價值(即使我們不見得能理解或換算那價值)時,忽然有一道長長的閃電慢速劃過我腦海。
如果我們能從植物的瀕臨滅絕上頭稍稍體會多樣性和變異性的珍貴,哪怕仍是用「未來或可發揮用處」來估量其價值,那麼,我珍視自己和其他人的多樣性嗎?
我能從自己身上重新認識「生物多樣性」這個概念嗎?
一個地域的一個生態系中,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物種。這些物種中,有的對此地適應性即強,自然繁衍了數世代數量龐大的族群。有的歷經試煉和漫長演化,好不容易才在此地存活,為了發展出更有利的生存條件,演化╱變異仍不斷在這些生物體內進行。換句話說,再怎麼艱困或肥美的環境,都有生命適應,都有彼此接納的方式。
能存活下來的生命,不都該為自己的多樣性和適應性感到成就甚至驕傲嗎?是那些明確或難辨的差異,讓我倍感艱辛或理所當然地活到了今天。而且還會繼續活下去。
我猜這是為什麼近日我經常想起王維詩中那滿山谷的璀璨辛夷花。管他有人沒人,它們都活下來了,活得那麼茂盛,花開那麼豐滿,紛紛開,紛紛落。它在自己的生物多樣性裡非常任性。
※以此文標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生物多樣性超級年」(super year for biodiversity)。
(本文首次公開刊載於 博客來OKAPI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