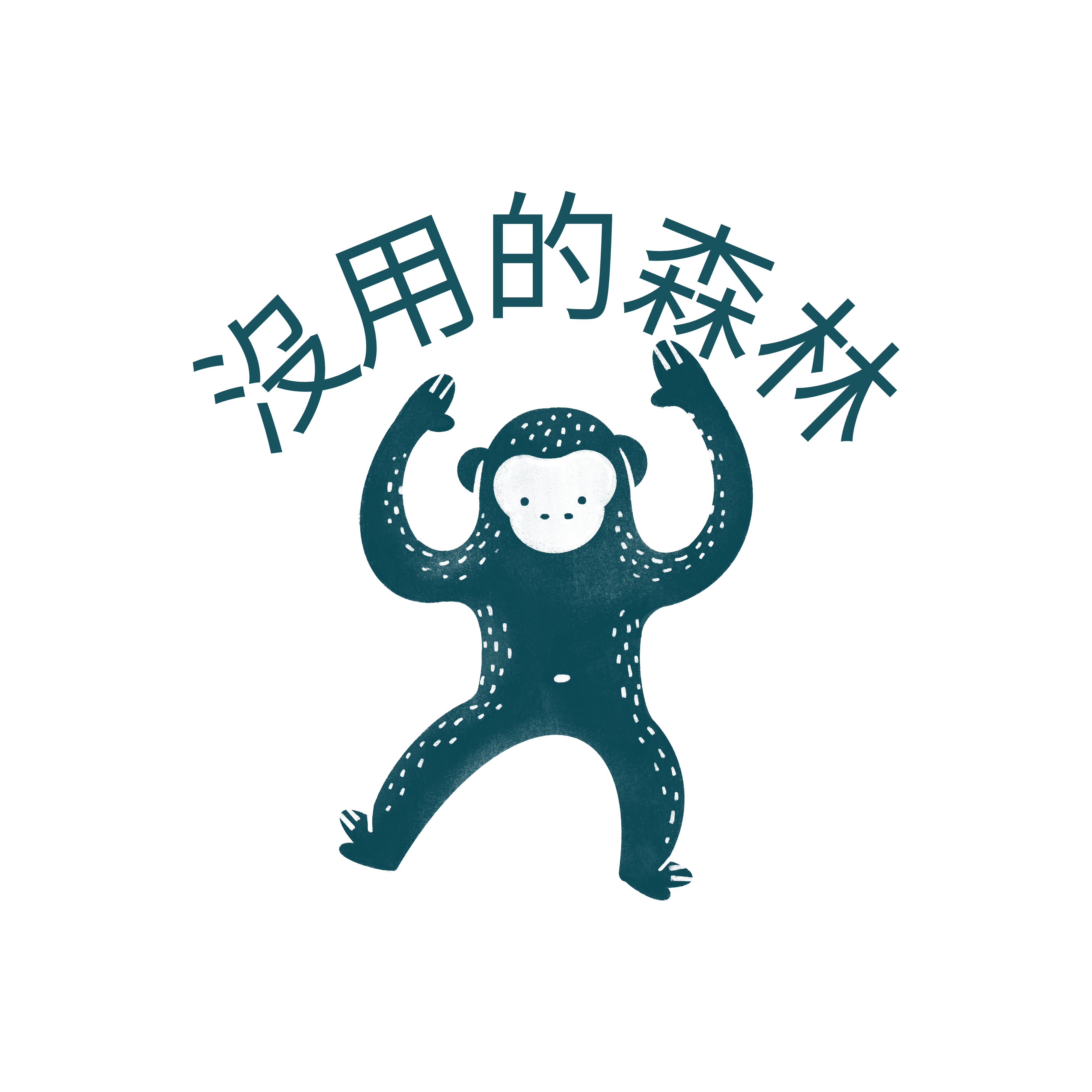那幾年看了很多舞,也認識不少舞人,當然,我們談話的主題多半是舞。可打從一開始,我就遇到挫折。舞人最常使用的語言是身體,換句話說,他們說話,可用身體說出的話比從嘴巴裡說出來的清楚。我記得工作初期採訪一個舞團,這群舞人找了劇場演員跨界合作,我先後訪問舞人和劇場人關於這個作品的概念和工作經驗,相較於劇場人邏輯清晰、能用具體例子輔助說明的表述方式,舞人使用的語言抽象且不容易理解。他們試圖以作品呈現一種狀態或感覺,但那是怎麼樣的狀態和感覺呢?他們思索片刻,最後站起身來做了一組動作,「就是這樣」,舞人告訴你,「觀眾感覺到什麼就是什麼」,他們不打算,或沒辦法以語言文字說明。
我問與舞人合作的劇場人,溝通時會不會有困難?會,劇場人習慣以討論或發問釐清彼此想法,於是常常被舞人唸「為什麼這麼愛問為什麼?」
舞人不用說的,他們直接做,劇場人這麼說。
但我因此陷入一陣長期的困惑:作為採訪者,我有義務取得受訪人的說法。說法:從他們口中說出,可被引述、被閱讀、被理解的句子。但舞人不給我。非不為也,更多是不能也。受挫的次數多了,我也曾訕笑舞人的不善言詞,一如有些舞人在談話中也會取笑笨手笨腳的不是舞人。
但工作總要完成。總不能老是怪舞人不會用字人的方式表述。慢慢地,去排練場看舞人工作跳舞,和他們交換有限的口語時,我慢慢調整自己從一個採訪者到一個身體和舞蹈的翻譯者。舞人不擅說故事,當他們試圖用夾纏的句子描述某種時空地點不明的情境或情感時,我會用話語幫他們重新編造、定義他們想表達的意思。當舞人說,「我想讓那個地方在舞者身上出現」,我問,「你的意思是你希望他的獨舞能在台上創造出你想召喚的那個時空或情境嗎?」「對,就是這個意思。」
當舞人起身示範一組動作,我學會在仔細觀察後和他們確認,「這組動作的速度比前一組快,而且用到更多手勢,所以你想透過這樣的質地傳達一種緊張的情緒給觀眾嗎?」「不完全是,我想用手展現重力的不同變化。」「所以不是情緒?」「跟情緒沒有關係。」
這樣的溝通越來越多,越來越順手。有段時日,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已找到某種轉譯和再現舞人與舞蹈的方式。過程中也不無收穫:我學到撇開概念、感受、敘事、意義這些我們習於用文字表述的抽象物事,回到更純粹,或曰本質的構成舞蹈的元素─線條、速度、精力、向度─去看一支舞。去談一支舞。
但舞蹈和舞人是否需要這麼被談論、被引導?面對舞人的身體和動作,文字儘管能界定它們,讓它們得以被廓清面貌形狀,但文字是否也扮演著農場籬笆一樣的角色,只能收服局部的舞蹈╱自然,而真正的、完整的舞蹈╱自然,仍野放於籬笆框限不了的畫面之外?
如果舞蹈的前提就是在敞開身體之際開展歧義的多條路徑,在某個必然的時刻,文字必然因傷舞而自傷。文字解釋萬物,但總有一些事物是文字無能收服的。文字可以使勁索討落實,但只能要到局部。你記錄得了線條、速度、精力、向度,記錄不了舞者利用這些動作質地同時向四面八方展開的對話。他們以身體在空間中訴說的話語,有時竟是超越了人耳能接收的獅子吼,於是再一次,我們只能依靠迴返自己的身體,用身體去接收而不是文字和腦子。
為什麼說文字傷舞而後自傷?因字而就舞的人,必然看到超出文字所能描述的意外,這意外或成驚喜,或真釀成意外,文字不精準的責怪隨之而來。從前我曾聽人批評村上春樹常在描繪事物時以「那個」(字旁且加註黑點)名之,是文學家偷懶的行為,我倒覺得不是偷懶,而是對神祕不可說之物的尊重。也許有時,文字面對舞蹈,也需帶上這加註黑點而不明說的尊重。
做為一個字人,比起直接觀看舞蹈,和舞人的相遇才真正觸動了我對舞蹈與文字相遇的更多想像。
「相遇」是個有趣的詞彙,它往往意味著不同性質的物事交會的瞬間,強烈的差異感乍然升起,卻還暫時與對錯美醜等價值判斷無關。我從對舞人的觀察、交談中學到,唯有盡量把價值判斷發生的時間延後,對差異的逼近、感同身受和理解才有更大的可能。
2006年,我因採訪工作接觸到的第一個舞人,是雲門舞集編舞家林懷民。那年他和爆破藝術家蔡國強合作的《風.影》,也是一次不同創作領域的相遇。在約一小時的訪談中,林懷民不只一次強調,他花了20年才把文字從舞蹈創作中卸掉。在成為舞人之前,嫻熟文學創作與新聞寫作的他原是個字人,但他說,文字傷舞,所以除去。
文字傷舞?怎麼個傷法?我沒多想多問,他也未再多說。但這四個字是漂亮的,我以一個字人的方式捉住它,將它留在訪談記錄中。訪談結束後,去看了《風.影》在嘉義演藝中心彩排,只記得影影綽綽,什麼也看不懂。許多年後我才明白,「看不懂」這三個字,傷舞,也傷和舞相遇的自己。
再次遇見舞人,是在雜誌擔任舞蹈編輯。剛上任時,我的缺乏舞蹈背景遇過幾次質疑:不是舞人,你怎麼傳遞舞人的訊息?但雜誌是字人的領域,以字和讀者相遇,不是舞人不是問題,怎麼用字傳遞舞,讓讀者藉由字和舞相遇,才是我要解決的問題。那段時日,文字不傷舞,是幫助我和讀者通向舞的重要引路人。
※首次公開刊載於《典藏今雜誌》2015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