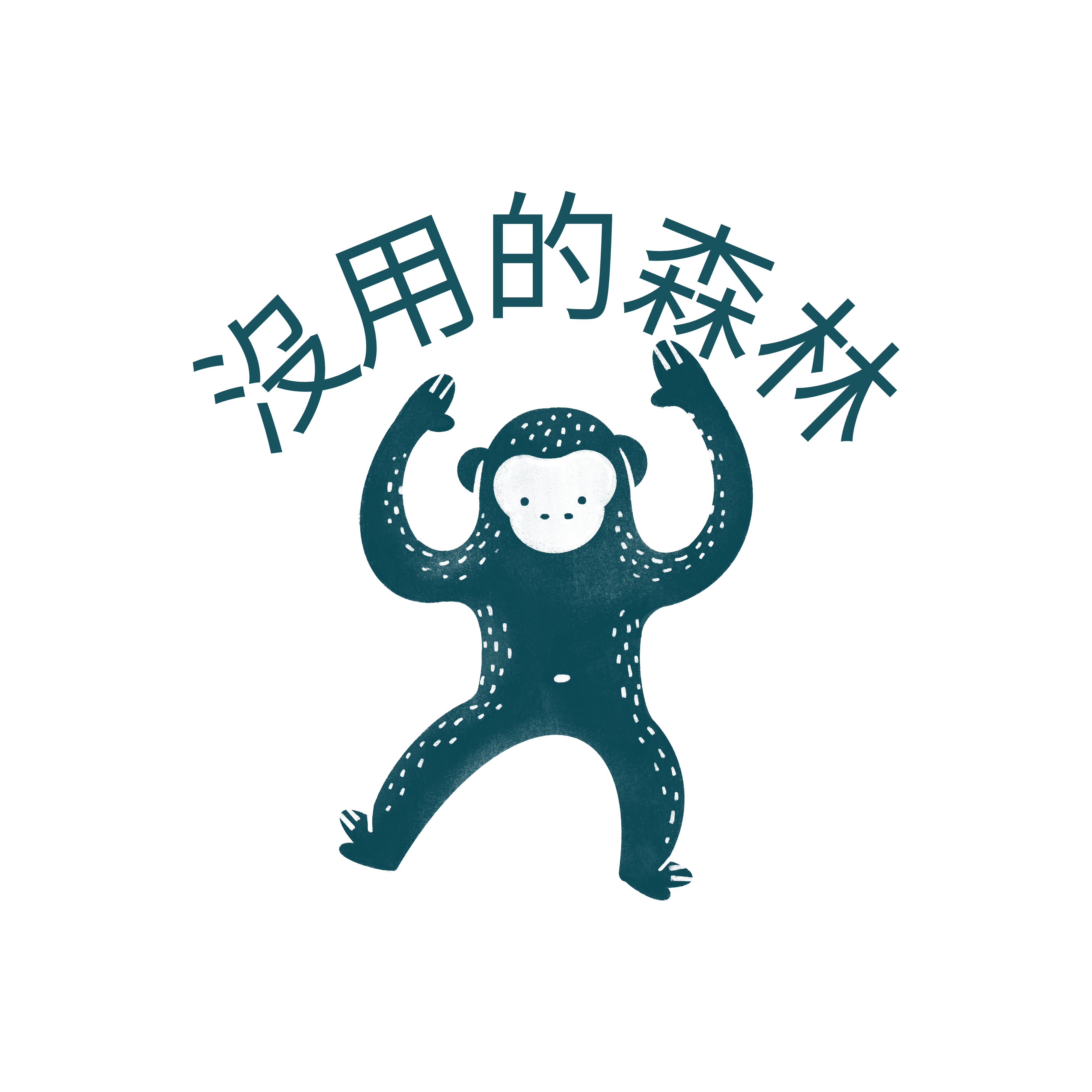一生啊 親像海湧啊
佇多情的海岸
慢慢行 來做伙啊
佇寂寞的海岸
——拍謝少年.〈北海老英雄〉
第一個觀眾從人群中漂起。她的四肢朝空中不斷甩動,靠著其他人的撐舉為她製造浮力,在半空中緩緩移動。台上的拍謝少年開唱不到三十秒,觀眾已經嗨到不行,接二連三玩起搖滾樂迷的人體衝浪(Crowd Surfing)。一首歌的時間,足夠五、六人從黑壓壓的浪中輪流升起,乘著音浪人海忘我前進。
那晚,作為東吳大學音樂祭的壓軸,拍謝少年一共唱了九首歌,台下觀眾也一路緊緊相隨,在舞台前方簇擁著奔跑著衝撞著跳躍著,所有身體席捲成一片海洋,無論陌生相識,搭著彼此肩膀,在〈兄弟沒夢不應該〉的巨大音牆中,一起噠啦噠啦的合唱。
設在東吳城中部遊藝中心一樓的舞台,無論設備或聆聽環境都沒法和LIVE HOUSE相比,但對即將期末考的學生來說,若能把自己徹底拋入音樂中,暫時忘記現實種種,這場音樂祭就算達成使命。舞台後方,一排小燈泡串起的白布條上寫著「逃海愚人號」,十分吻合音樂祭的主題「逃亡吧!都市漁人!」。網路上的宣傳文案不知是否同樣出自學生之手,如果是,不禁教人疑惑:大學生,依然是社會大眾認為更有理想和夢想的一群人嗎?
「討的是生活,逃的是人生」。在這世故的感慨下,他們吆喝眾人:「跟我們一起逃亡吧,都市漁人們╱逃離城市的燈紅酒綠,掙脫世俗的限制╱往大海的另一端前進」。
海的另一端有音樂,有陌生人相伴同歡。在這氛圍中,過早來臨的討生活壓力得以退場,青春仍是一把想燒就燒、勢足燎原的柴火。或許因此,儘管六月巡演特別多,拍謝少年對東吳這場Live的印象依然深刻。
「超誇張的!」對那晚群眾不停飛起如魚或浪花,貝斯手薑薑想起來,忍不住又嘆了一次誇張。吉他手維尼對那場演出則有點不習慣,「一走進去這麼多年輕人……」
通常,拍謝少年的現場聽眾平均年齡會再大上那麼一點。薑薑、維尼和鼓手宗翰今年三十三歲,他們想像的聽眾是自己年紀加減三歲的族群,東吳那晚,這群人同樣在場,只是退到離舞台稍遠的地方,而他們的聆聽習慣也和青春勃勃的學生不同,多半手拎啤酒獨自站著,閉眼輕輕擺動身軀,或只是冷靜觀望台上熱火朝天的表演。
去年十二月,拍謝少年總算發了第二張專輯《兄弟沒夢不應該》,距前一張《海口味》已五年。半年下來,他們跑遍全台,除了台中、台北、高雄的Live house三次大型專場演唱會,從前期募資到宣傳後期,他們一路唱遍麻辣鍋店、保齡球館、客運轉運站和大小音樂節。這些密集的演唱行程,讓表演者和聽眾之間的關係不斷進化,明明拍謝並不是擅長營造互動的樂團,但「觀眾的怪招好像越來越多」,維尼笑說。
扛人、繞圈、甩髮、衝撞,這些搖滾樂迷習慣的招數,拍謝觀眾自動自發玩得起勁,台語搖滾之於這群年輕人,能否從頭到尾琅琅跟唱雖不得而知,但他們總會找到合適切口,滑進拍謝少年的樂曲片段用力合唱,再滑出去繼續推扛彼此,用身體回應旋律。
「我們很希望跟觀眾一起變老」,三人不約而同說。問他們對一起變老的想像是什麼?薑薑想起幾年前去聽美國搖滾樂團Yolatengo的演唱會,這支成軍於90年代的團體,早期樂風偏噪音,後期製作許多小品,一直是他們樂迷的薑薑形容,在演唱會編制中聽見一個樂團遼闊的生命幅度,「那是我很想達到的境界」。
「我的想像是大家到最後都像朋友」,維尼說,跟樂迷認識,聽他們的人生經歷,對身為創作者有其意義。畢竟人類再怎麼進步,都是喜歡聽故事的,若能把眾人的故事轉化成音樂等形式再訴說,「可以豐富彼此的生命,而不只是留住你的(演唱會)票錢而已。」
但,「跟歌迷一起變老」,在台灣獨立音樂圈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逃海愚人號」現場,面對台下的狂躁青春,拍謝少年有感而發。東吳畢業的宗翰憶起上次在母校演出是十年前,「那時候跟我們同台的樂團都消失了……」
薑薑則被東吳校園內一間「生涯規劃室」觸動。在舞台上他說,想把接下來的歌「獻給十年後的你們」,「願你們那時候還這麼愛搖滾樂」。
場下一片鼓譟,幾個年輕男孩一齊脫掉上衣,在樂聲中蓄勢待發。
揣無頭路彼幾工
覕佇厝內 毋敢來哭出聲
伊感覺家己是一个抾捔的人
煞來賭氣分西東
講伊欲來怨嘆一世人
這馬的生活 已經是滿滿孤單
——拍謝少年.〈骨力走傱〉
得知拍謝少年與《新活水》編輯室共同對台灣年輕樂團擬了一份訪綱,吉他手維尼也參與採訪工作,回故鄉高雄訪問幾個樂團,不禁好奇這三位跨過三十而立的晚期少年,如何看待小他們近十歲的樂團新世代?
維尼率先提出異議,「我很反對用世代定義,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不一樣」。
這話題在拍謝之間引起一陣短暫辯論。宗翰提出的「厭世代」三字被維尼反駁「沒和每個人談過不能就這樣貼標籤」,儘管他們都同意:二十幾歲的樂團確實呈現出「在創作上更關注自己生活、而非社會議題」的集體傾向。
「但也不是厭世……而是不會主動說要把音樂變成武器去抵抗什麼」,維尼說。
「我覺得是世代落差」,薑薑認為,和他們這一代樂團不約而同關注社會議題相比,二十幾歲的樂團的確比較少用音樂表達對社會的關注,但他也想透過提問確認這是不是自己的刻板印象,畢竟,2014年3月那場大型社會運動中的年輕世代「很不一樣,超級關心社會議題」。
「但是這個下來大家都是疲勞的啊,而且你也沒有真的改變什麼。」維尼說。事實上,從樂生、反旺中、華隆罷工、反核等議題和抗爭,拍謝都曾親身參與或獻聲演唱,但眼下維尼卻提出一個反問:「如果從流行音樂推廣的角度來講,樂團為什麼一定要關心社會議題呢?」
當流行歌手不被要求一定要關注社會時,樂團卻必須面對「有沒有關注社會」的自我質疑,社會議題成了一道弔詭的枷鎖,檢查著樂團是否有作為樂團的資格。
維尼強調,在他採訪的過程中,有些樂團或樂手並不是不關心社會議題,而是一旦把他們視為一個集合體,他們會不知如何施力,更別說把社會關懷變成音樂創作,「有些人就是寫不出來啊!」
維尼以一位正「陷入生命巨大失落」的樂團受訪者為例,「我覺得他正在生命很可貴的狀態。他在一個努力過後的低點,但還是想盡辦法療傷自己。這種時刻如果再說他是『厭世代』,人家就是在一個很衰小的狀態裡,你叫他關心社會幹嘛?他又不是時代力量候選人。他一定要先讓自己好起來啊。」
「我會用另一個觀點來看」,陷入一段長考的薑薑出聲,「如果你今天是藝術文化工作者,本來就在做觀念或概念的傳遞……如果你受到比較多注目,你可以把比較少人關心的議題透過擅長表現的形式去做溝通,這件事對我來說滿正常的。你當然可以只寫戀愛或恐怖(題材),但如果你有能力,對這事情也有感覺,去做這件事情不也滿好的?是一個正向的力量。」
「畢竟我們滿受濁水溪公社、林強這些前輩的影響」,宗翰提到當年初聽這些創作者的作品,對裡頭的社會批判不由浮現「幹!好屌!」的感覺,這些歌曲直到今天依然留存內心、打動自己,「你可以說是內容議題,也可以說是藝術形式打動我們。對我們來說,是這些東西影響我們創作,所以我們也希望在作品中傳達這兩種元素。」
我問他們,有沒有可能這些年輕樂團終究得花大把時間「骨力走傱」,所以難再分心力給公眾事務或社會議題?畢竟,不少受訪者是靠一萬五到兩萬元的打工費度日,或正在償還學貸的迢迢長路上。
他們並未直接回答,而是給我一個採訪後的反饋:與其在意這些年輕人一個月靠樂團賺一萬還是六千,「其實都一樣,都很慘」,透過這機會認識他們的想法和更立體的樣貌,或許才是重點所在。回到他們自己,其實也很少和圈內朋友聊「能否靠樂團維生」一類問題,「對方要不很爽、要不很賽,很爽的我不會太在乎,很賽的我會心痛,但也沒辦法幫他們,因為我們也是花了很久才顫巍巍地站穩……」
兄弟無夢 不應該
你感覺一生希望袂來
稀微的人怎樣鬥陣
你感覺無心無目屎
頭前的路 忽然間
你看著一生希望的愛
怎樣來做 無人教你
咱只好心肝放輕鬆 啊
——拍謝少年.〈兄弟無夢不應該〉
和拍謝少年約訪不算難。他們沒有經紀人,對外聯繫全靠團員分工打理,唯獨一個不成文規則:要約任何周間行程,務必在晚間八點後。如此,白天是上班族的薑薑和宗翰才能準時赴約。
不只媒體採訪如此,練團也一樣。朝九晚五的工作結束,繼續趕到位在大安區的和平阿帕練個兩三小時。約周末假日練團或許較從容,偏偏六月邀演特別多,周末的時間給了台南、嘉義等地音樂祭,連平常日也難得碰上一周內演出四場的高頻率。
「這不是一般狀況,通常一個月頂多兩場」,薑薑說,一旁宗翰補充,「平常很難得周間排兩場表演,這對上班是超大壓力。」
去年底發新專輯《兄弟沒夢不應該》,企劃巡演才剛在五月底結束,六月接踵而來的邀演,可說是口碑迴響的具體反映。然而,五年籌備一張唱片,光企劃行銷就花了一年,最後衝刺般進行募資、拍MV、辦演唱會……雖然有廖小子、柯智豪、李文政、姚登元等有才情的前輩和兄弟支援,這場長跑仍不可避免地帶來筋疲力盡之感。
何況他們都另有工作在身。薑薑目前任職食品業,負責產品開發和行銷,宗翰在專辦音樂節的公司上班,維尼是吉他老師,上班地點就在阿帕。前面兩人過的是一般上班族時程,維尼的時間彈性較大,但他自嘲收入「就是一個高級工讀生」,加上必須配合學生時間,工作多在夜晚或周末,不得不錯過許多想看的表演。
問他們從玩團之初就預見必須這麼分頭兼顧理想與現實嗎?宗翰不疾不徐地回顧:從十九、二十歲到地社、春吶看表演,就發現大部分玩團的人無法靠樂團維生,許多人會選擇到Live House當企劃、PA、燈光師等職。起初,薑薑和維尼也曾到音樂公司做宣傳、企劃等工作,但後來,「半年多就覺得這行好累」的薑薑選擇了與音樂無關的產業;維尼則在工作十個月後認清「對幫別人辦表演的熱情就到這裡」,此後專心教琴。
宗翰除了音樂也著迷於電影,曾在不同影展工作,但影展工時往往密集壓縮、沒日沒夜,直接影響練團,「如果繼續做下去,樂團就沒辦法發片了」。只是,回到音樂產業,宗翰發現,「好像只有旺季沒有淡季」,「基本上一整年都很忙碌。」
白天討生活、晚上玩音樂的日子就這麼過了十多年,隨著《海口味》、《兄弟沒夢不應該》面世,音樂圈對「一尾土產台語搖滾樂隊」的拍謝少年評價日益升高,但,這些反響在撞上「跑完專場、還拿補助,結算下來,沒有賺錢」的現實後,三人仍須苦惱面對「接下來該怎麼走」的難題。
「解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維尼說。雖然這選項從未被三人正式提出討論,但私下,他們各自心知肚明,這堵牆無時無刻在那裡。
從出社會工作到結婚成家,薑薑一直是三人中最快的那個,接下來將走到「生子」這一步的他,某程度也是兵臨牆下壓力最迫切的一個。
「現在真的很ㄍㄧㄣ」,他嚥下一口生啤,「假設樂團是你喜歡的生活方式之一,可是它不賺錢,可是你又想要有一個普通的家庭生活,這件事就一直在一個edge(刀口)。我是一個幾乎沒有休息時間的人,工作壓力很大,加班時間也很長。非常intense(緊張)。那個intense會影響很多事情。如果照這樣下去,我覺得不是健康的。別人看起來都ok,你有處理好大家對你的期待,可是你自己可能受不了。你一直都在『這些事情都要做好,才可以拿到一個好的pay;這些事情要做好,才可以有一個好的performance;這些事情都要做好,才可以有一個好的關係』……」
不知不覺,他面前的啤酒杯早空掉喝完。「太intense了」,「我希望我不要這麼ㄍㄧㄣ,才有餘裕創造另一個生命,陪他長大」。
「我想我們可能都有點貪心,覺得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不用靠音樂賺錢一樣可以生活……但真的不可能兩件事情都做到極端」,宗翰露出苦笑,「這是矛盾的,你不可能變成(工作)年收入兩百萬又同時去小巨蛋開唱。」
宗翰坦承其實自己經常想到放棄。「當我的狀況不允許做這麼多事情時,真的很累。我不知道還能夠怎麼做。龐大挫折感襲來時會想:幹,不如放棄好了。工作跟練團都要花很多時間,兩者衝突時我常想要不要做出抉擇?」心裡的聲音選哪邊,他沒說,「我好像不是靠著自己的意志力說好,一定要繼續玩下去,而是看到他們也還在堅持做這件事情,也沒說要放棄,如果我現在說要放棄,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很累很累的時候,累到不知為何而戰的時候,他會大演抉擇或放棄的內心戲,但「那時候就會覺得他們都還在,音樂這東西,還是你可以抓住的……當我自己打鼓時,就會覺得自己還活著,不是一個工作機器。不是現在什麼事情來了就要趕快去解決。只要把自己丟進去(音樂)就好。」
「對樂團來說,某程度可能是『做愛後動物感傷』吧」,薑薑這麼形容近來流竄於三人間的龐大疲憊感,「因為我們完成一件滿不錯的事情,在能力可及的範圍內把事情完成得不錯。」
感傷的部份原因,或許也跟一路與他們青春相伴的濁水溪公社近來宣布即將在2020年解散有關。主唱小柯的理由是:對於社會,他已經沒什麼話要說。
「你要怎麼說服自己可以繼續?或說,假設你是火車,有什麼樣的柴火可以讓你再往前跑?」小柯的宣言和近來與焦安溥的一席談話,讓薑薑如此自問。
對維尼來說,他的柴火在家鄉高雄。這半年來,他往返高雄的頻率變多了,雖然回去也沒特別做什麼,不外「拿個飲料香腸坐在海邊,然後三個小時就過了」,但這樣放空的時間感,在台北就是得不到。「我的工作在一個超級小的房間,每天就是十小時關在裡面,出來時眼睛濛濛的,也不知道幾點,就這樣離開了。那種生活非常破碎,反而在路邊發呆,對我來說比較有活的感覺。」
至於薑薑的柴火呢?
「有時會有歌迷寫信給我們,說有一天他租的地方大漏水,又下雨,水電工人又叫不到,那天他都在聽我們的歌,他寫說,那時候是我們的歌跟他一起在那裡。偶爾我們會收到這樣的信。那滿給你柴火的,讓你相信自己可以繼續燒某些東西。就像我自己喜歡的那些樂團,他們也陪伴我很多時候,而我也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給別人這樣的感覺,哇,那麼幸福。」
這是咱的時代啊
骨力走傱幾若冬
日思夜夢的未來啊
山盟海誓鬥陣行
——拍謝少年.〈骨力走傱〉
「拍謝三個人的質地很好」,擔任《兄弟沒夢不應該》製作人的柯智豪本在談專輯製作的過程,忽然彎一拐,劈頭就給了拍謝一句贊詞。
問他拍謝怎麼個好法?「首先熱情很重要。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喜歡』,我喜歡這個、喜歡那個,他們的火還在,這個很好」,火沒被生活的龐雜瑣碎熄滅,對大他們十多歲、自稱「做到三十幾歲就沒那個熱情」的柯智豪來說,是非常難得的特質。
難得也在於,是他們三個人,薑薑、宗翰、維尼,組成了這個拍謝少年。「他們可以湊在一起,把環境跟氣氛保溫起來,留著那個兄弟的『氣』是很難得的」,柯智豪說,氣味很重要,但更可貴的是,他們的溫度和熱情會移轉、覆蓋到觀眾身上,「所謂自己的氣味不是這麼好掌握的。拍謝的音樂會長這樣,因為人就長這樣。這也是一種成熟」。
說起來的確是難得。在台中長大的薑薑跟宗翰,為了一睹獨立樂團的現場風采,相約考上台北大學。利用多得不得了的大學時光學鼓和貝斯的他們在BBS站台批踢踢上找人共組樂團,維尼是第二個回信的。內向不善與人交際的他,抱回夢寐以求的電吉他,卻發現只有一個聲音單打獨鬥的音樂,是多麼無聊。一拍即合的三人在恆春看完春吶後,被雷打到一樣開始創作,試著把他們從伍佰、陳昇、林強等音樂創作者汲取的音樂養分,澆灌成自己的旋律和歌。
對大學才正式接觸搖滾樂的他們來說,起步雖跌跌撞撞,卻也將三個人黏合成堅實的共同體,「我們先是朋友,才是樂團」,維尼說,跟其他練完團喫支菸就掰掰的樂團不同,他們漫長的青年時光多半共度,一起騎車出遊、打籃球、看電影、一起租屋共厝(宗翰說那陣子警察常找上門,因為三人在家練團噪音屢被左鄰右舍投訴,「可是真的很方便啊,我們就這麼近!」)……
也不是沒爭執過,但三人性格互補,一如創作和演奏時,注重細節的薑薑和表演較衝的維尼在宗翰賦予節奏和定位的鼓聲中找到一致的步調,形容自己跟維尼都是「歹鬥陣」的人,薑薑說宗翰的圓融能緩衝兩人偶爾意見不合的氣氛,「維尼太衝或薑薑太龜毛,我就把他們拉回來一點」,宗翰也幽默看待他們的鐵三角關係。
或許是這樣的關係造就了拍謝少年講究均衡的集體創作模式。不像多數樂團由主唱或吉他手專責詞曲創作,其他人負責配器,他們的旋律和編曲多在練團室以即興拋接(jam)進行,歌詞則由唱的人填寫。以最晚寫成的〈暗流〉跟〈骨力走傱〉為例,三人皆有唱段,等於整首歌是採即興和接力創作的方式完成。
當然也會有串不起來而放棄的段子,但已有默契的三人更常出現的狀況是jam得一發不可收拾。薑薑說,他們的歌少有流行歌曲「ABAB」或「AABA」結構,而是一路堆疊發展有如長篇敘事的史詩結構。這或許源於後搖曲風的滋養,維尼認為,和他們愛看的台灣電影如《南國再見南國》、《美麗時光》中奇特的流動感也不無關係。
提到史詩和敘事,拍謝以腔調生猛厚重的台語填入後搖基底的曲調,自然成為討論重點。「它應該是我們所會的語言中最具音樂性的。當然我們對台語歌的吸收很徹底,jam的時候就會很自然流出來,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台語在作宣示時是很帥的語言,跟搖滾樂的重或陽剛很接近」,維尼說。
薑薑也用嘻哈音樂裡的”punchline”來比擬他們對台語歌詞的選擇,好比〈骨力走傱〉裡出現的「山盟海誓」四字,「它的韻很漂亮,而且一聽就懂,所以你很常在台語歌裡聽到它出現」。
歸根究柢,他們希望創造的是真正著根於台灣在地的音樂,就像他們經常提到的濁水溪公社,「怎麼可以把搖滾樂玩得這麼台、這麼妙,只有我們懂那些笑點,這東西真是出了台灣沒人可以做到。小柯是看豬哥亮綜藝秀長大的,卻可以成為台灣經典龐克團,身為台灣人可以看到他這樣轉化台灣文化,我覺得非常幸福。」
「重要的是那東西你會唱。在你生命很重要的時刻,會想唱伍佰,而不是Bob Dylan」,薑薑說,「怕鬼的時候一定是唱伍佰,唱洋文一定更怕」,維尼搞笑補充,「唱歌、怕鬼、罵髒話,一定是說母語!」
用嬉鬧與執著織就的少年時光,就這麼迤邐著走了十多年。儘管隨著踏上不同人生階段,三人的生涯有了時差,只要一起站在練團室或舞台上,音樂就會讓他們逐漸聚合成一個彼此支撐、彼此抗衡的三角形。問他們:為什麼總在台上站成三人相對(而非面朝觀眾)的模樣?在演奏中,他們到底如何感覺彼此的存在?
「我到現在都還覺得是,vanish in the sound,一起消失在聲音裡」,薑薑說,那是一種平常不太能體會到的感覺,但玩團可以,「消失的時候,那種超越軀殼的感覺,可能是最大的自由」。
宗翰也感覺到相似的狀態,「自己可以跟樂器的聲音一起消失在那片空氣裡,即使是現場演出的時候」。忘我的感覺危險也甜蜜,有時他必須在這巨大的聲音之海中鬼吼鬼叫,在全然淹沒中探出頭,用存在去印證消融發生過。
拍謝少年其實可以理直氣壯、毫不拍謝(sorry)的。既然他們已那麼多次遠征,深深潛入那海。
本文首次公開刊登於新活水雜誌 網站暨 紙本2018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