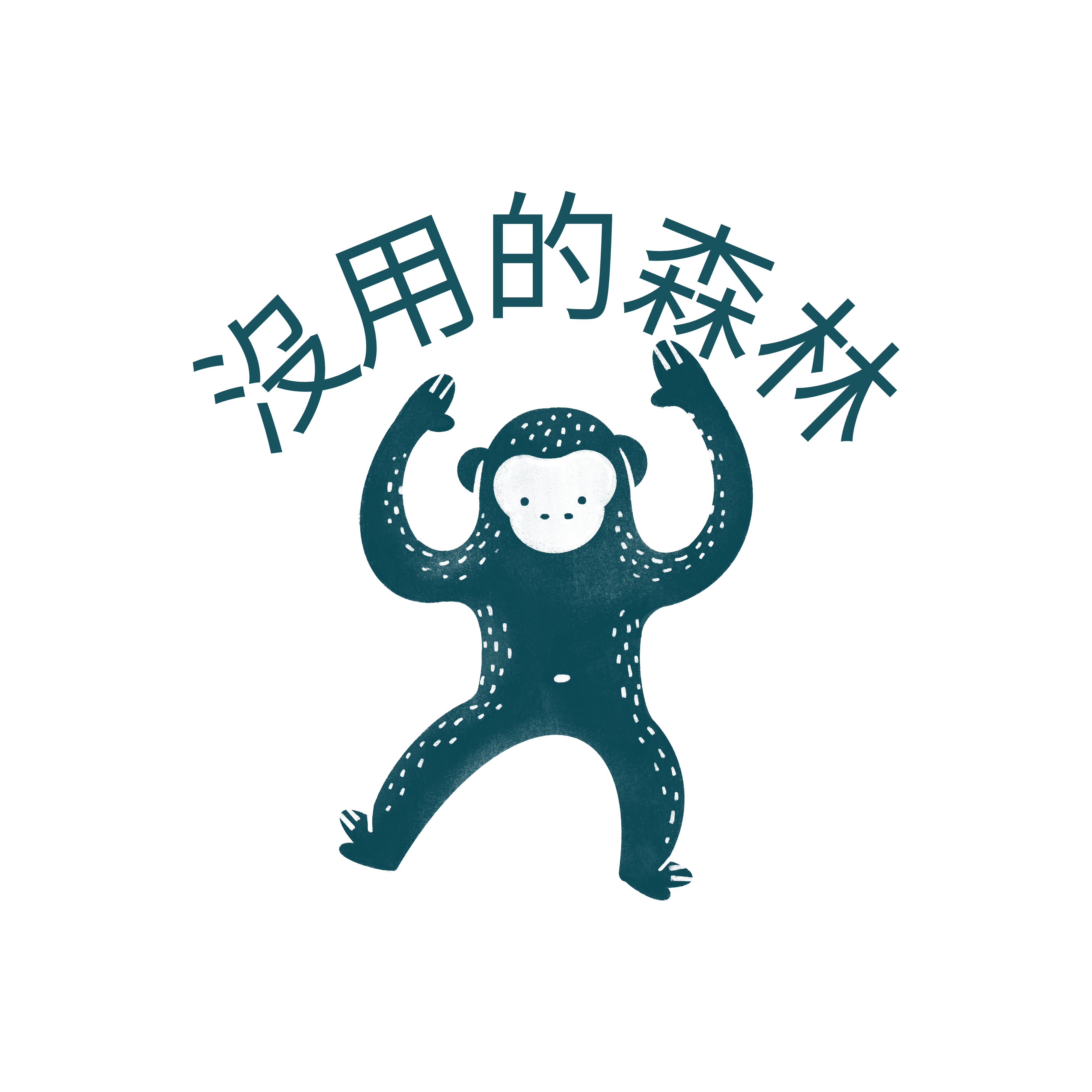宜蘭一處無人海灣上,有四個人彎著身體,在植被並不茂密的砂地上不住尋找。偶而一聲興奮的「找到了!」隨即又懊惱更正,「看錯了……」
他們在找的,是一種名為「列當」的植物。據說,很久很久以前,從海岸到山地,台灣隨處都可見到列當的身影,然而,和其他受威脅終至瀕臨滅絕的生物一樣,不知不覺間,列當從人類的日常生活中隱遁,想再見到它,必須發揮偵探的功力,在特定時間前往少數特定地點展開地毯式搜索,好比這四個埋首於海岸低矮植叢間的人。
這四人當中,有兩個是經驗老到的「尋花人」,另外兩個是經驗值零、卻忍不住也跟著找起來的我和攝影師阿煇。我們要從方圓五十公尺的植被覆蓋地上尋找符合以下特徵的植株:
株高15-40公分,全株密被白色絨毛,花序部分較密。具地下塊莖,肉質,粗厚肥大,單一不分叉,暗黃褐色。葉互生,鱗片狀,披針形,先端漸尖,長8-20公分。
儘管知道列當的特出之處,就在於它不是通體綠色,而是和中高海拔的明星植物「水晶蘭」一樣獨特的白色,對找植物的新手來說,依然如大海撈針,更別提尋找列當的這天,海風呼嘯不絕,雨水時歇時驟,在風雨中尋找一株列名紅皮書的瀕危植物,象徵意味不能更濃厚了。
尋找列當,這個任務是尋花人之一的山野人提議的。本業是計程車司機的他,自從十年前買了一台數位相機,就踏上了尋花覓草、拍攝植物之路,也從一個對植物全然陌生的新手,變成擁有5000多人的臉書社團「台灣野花366尋花記」的幕後推手。
這個植物社團的人數並不多,卻像一群高手行家聚集交流的祕密基地。所謂高手行家,不只擅長發掘野生植物的美好(且擁有夠好的相機或拍攝技巧捕捉其美好),更具備「追植物」的技能和狂熱,他們不只知曉許多台灣野生植物的分布位置、生長時序,也謹遵一套尋找、觀賞、拍攝植物的倫理規範。
在社群平台眾多的植物主題社團中,「台灣野花366尋花記」因推廣野生植物之美和強調植物拍攝倫理而顯突出。
衝著有許多台灣原生的野生植物美照,很久之前我就加入社團當純欣賞的潛水成員。但能認識社團管理員、甚至和他們一起出外找植物,是福山植物園牽起的機緣。
福山植物園負責「方舟計畫」瀕危植物保種的林建融曾提到,或許是研究員的工作屬性,早期他習慣獨自埋頭苦幹,不太跟人交流,但開始著手方舟計畫後,他花了滿多時間跟民間的高手行家交流,「我希望讓他們了解,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過去有些民間的植物愛好者認為,林試所將受脅植物從原棲地帶走,是以保種之名行盜採之實,林建融靠著打入社群直接對話,逐步建立信任感。對經常拍攝稀有植物的人來說,不曝光植物族群的位置,避免人為採集或干擾棲地是基本倫理,那當中儘管也有自利心態——希望每次去都能再見到、拍到美麗的植物,卻不是自私。在充分說明移地保種的重要性,以及方舟計畫和民間自行採集保種的關鍵差異後,林建融獲取了一些民間人士的信任,他們慷慨和他分享自己所知的稀有植物點位,甚至帶他去看。
「別人帶我去現場指給我看的植物,我絕對不採。必須要讓他回來還找得到他的老朋友」,林建融這麼說。
在福山採訪時,剛巧就有這麼一位民間人士來找林建融。那天,山野人剛好載了一台包車客人上福山,順道帶一盆植物給林建融託管。那盆不起眼卻長勢旺盛的植物叫「禾草芋蘭」,明明屬於台灣原生蘭科,卻冠上「禾草」二字,不起眼如雜草的外觀可以想見;但它的另一個名字「美冠蘭」,清楚表明了開花時的它,容顏將多麼妍麗。
這盆禾草芋蘭是民間愛花人輾轉搶救而來的。多半生長於南部荒地的禾草芋蘭,因棲地土壤被人為搬運、挾帶,偶爾能在中北部看見,這棵芋蘭就是野花366的社團成員在土城一處工地所發現。友人趕在工地施工前救回植株並交給山野人,但他們一直找不到合適棲地移植,得知植物園目前尚未收存禾草芋蘭,便交託林建融照管。
不同於林試所專業的受脅植物採集人,像山野人這樣的業餘植物愛好者,是怎麼變成追植物的人?帶著這樣的好奇,我們有了風雨中尋找列當的旅程。
「我們常開玩笑說,山野人去哪裡找植物,我們就不要去」,拿山野人出門必逢下雨嘲笑的,是另一位尋花人張家昀,她是野花366的管理員之一,也是山野人因尋找野花結識的忘年交,當年促成他們相識的植物,就是列當。
因攝影而迷上植物、相關知識全靠自學的山野人說,大學念生科、辨識草本植物很有一套的張家昀是他的植物老師,每次在野外拍到連圖鑑也查不到的植物,問張家昀通常就能得到答案。其實,這一天要不是正好遇上農忙,我們本來找植物的地點,會是張家昀和其他夥伴共同成立的「新南田董米」所耕種的水田。
和一般慣行農法田埂上光禿禿沒有任何植被的水田不一樣,新南田董米以友善生態為前提,兩個研究鳥類的主理人希望心愛的鳥兒能跟農地共生,選擇在蘭陽溪出海口,這片土壤偏鹹卻是眾多候鳥留鳥棲地的區域耕種。喜歡植物的張家昀,也順理成章地以田地四季生態為觀察對象,光是一條短短的田埂,就可以找到美洲母草、擬櫻草、心葉母草、水蕨、開卡蘆、雙穗雀稗、石龍芮……十幾多達七十多種野生植物。
一條住滿你認得名字植物的田埂,和一條被水泥化方便管理的田埂,差異固然不能僅從生態倫理評價,兩者得失也難以時間金錢效益斷定。
不過,這些效益或價值,對於從台北移居宜蘭的張家昀來說,或許再清楚也不過。雖然宜蘭的氣候多雨,濕氣不但養出牆壁、食物上的黴菌,也讓她動輒筋骨酸痛,但她還是愛極了融入自然,成為溼地生態一份子的工作與生活,心血來潮時還能抓起相機,跟山野人等社團同好一起出野外,尋找「待拍清單」上的植物。
我問山野人和張家昀,每次外出找植物會定下目標嗎?兩人皆搖頭,「通常不會針對特定植物,來到一個地方,有什麼植物就看什麼、拍什麼」,山野人說,由於在宜蘭開計程車多是外來觀光客包車行程,每到一個景點,客人往往停留半小時到一小時,他就利用等待時踏查附近的野地荒地,當年就是這樣踏入拍攝植物的領域,後來也常因此邂逅美麗獨特的野生植物。
「對我們來說,自然觀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張家昀附和,笑說就算定目標,也未必能如願前往尋訪,好比山野人多年前就想拍的大蜘蛛蘭,雖然採訪時正值花季尾聲,社團經常有人貼出美照,但他還是抽不出空檔尋花,只得等來年。
正疑心這趟列當之旅會不會空手而回,畢竟列當花季剛開始,而這些年氣候變遷讓物候更難以捉摸,忽然,山野人連聲喊著「找到了!」眾人湊過去,只見他打開相機,蹲下身靠近一團纏繞的藤蔓,對著上頭結的小果不住拍攝。
這不是列當,而是一種名為「無根藤」的植物,雖屬樟科,型態卻和我們熟悉的樟樹大異其趣。山野人邊拍邊喃喃:「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它耶,我想拍好多年了,雖然它不算難找……」他一臉滿足笑容,「今天好驚喜喔!」
這樣的驚喜固然是追植物的人心中一大動力,但也有一種動力,來自不屈不撓地尋訪和等待。為了一睹分布在有限低海拔山區的「小豆蘭」開花,山野人曾連續開車前往棲地八次,才看到含苞許久的小豆蘭綻放。那是值得銘記的經驗,因為接下來兩三年,小豆蘭不曾再有花苞。
張家昀也有類似的體驗。「水玉杯」是一種極為罕見、體型微小的腐生植物,棲地不僅狹隘,還隱藏在落葉層裡,必須小心翻找,尋找難度堪稱五星級,「這種一定要人家跟你說才找得到,所以我一聽有人找到,隔天就開車去看」。
當偶像追星族或可理解,但追植物,且不是基於研究的理由,這點恐怕不是一般人能懂。然而,在埋頭尋找列當時,我模模糊糊體會到一種幾近「尋寶」的樂趣。我沒玩過先前流行的寶可夢,但據說找植物的過程和玩寶可夢遊戲有幾分相似。這說法或許有其道理,畢竟寶可夢的起源,就脫胎自企劃者田尻智童年尋找、收集昆蟲的回憶。
張家昀和山野人指點我,要從茫茫植被中找列當是需要「撇步」的。列當是寄生植物,必須倚靠宿主茵陳蒿才能生長,所以先找植株較多的茵陳蒿,再往四周尋覓列當蹤影就容易多了。
茵陳蒿有著菊科典型的葉型,找起來果然不難,但有茵陳蒿未必就有列當。其實,這兩種草本植物長久作為中藥草藥材,一直都有過度採集的問題,加上外來強勢植物佔領棲地,它們的生存空間也只能不斷限縮。列當面臨的採集災難又遠勝於茵陳蒿,挺拔直立的白色外型,加上紫色花穗,對酷嗜「以形補形」的人來說,列當等同壯陽補腎的良方——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又是山野人的高呼,「真的是列當!」他指著地上一枝頂端如戴棕色錐帽、身形細長、白色間綴棕色斑紋的小株,不知是置身風雨太久或是列當自帶仙氣,看著它竟有幾分親睹小精靈之感……
接下來,果然就如張家昀所說的,發現第一株後會接著發現更多,我們接連找到已冒出紫色花穗的一大兩小三兄弟、隱藏在朽木下剛竄出頭的三小列當……在那片海灘旁的砂地上,我們一共找到了十二棵列當。
只要發現列當,稍作觀賞,眾人便拿起手機相機不停拍攝,若是植株的位置四周有其他植物的枝葉遮蔽視線,山野人也只用手輕輕撥開它們,待拍完後就讓它們回復本來位置。要是列當遠離主要路徑,張家昀會選擇站在原處,以鏡頭拉近焦距拍攝,山野人則找不會踐踏太多植物的方式靠近拍攝特寫。
除了兩人拍攝風格不同外,這些行動實則反應了他們拍植物拿捏的倫理分寸。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原則:盡可能避免干擾和破壞棲地生態,棲地裡除了你關注的植物,也有其他植物、真菌、昆蟲和動物棲息,不能只顧著眼前的奇花異草而漠視周遭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利,不假思索讓你的舉動損及生命。
張家昀說,他們很少舉辦社團出遊外拍的活動,就是怕人多對棲地造成壓力;山野人提到,有時他會在人工步道旁拍攝,若遇到路人經過好奇詢問,他甚至會隱藏自己拍攝的目標,假裝拍鳥類或昆蟲,低調再低調,「就是為了保護植物」。
儘管社團中多數成員都懂得自律以尊重生命,他們還是氣憤說起,近年屢屢聽說有專拍珍稀植物的人會摘除花朵,不是因為貪戀花的姿色,而是為了自己佔據獨家畫面。也有人把附生在樹上的植株連同樹皮一起割下帶走,他們推敲是因為拍攝者久候花期不至,索性帶回家等它開花。
「這是我們越來越低調的原因」,如今山野人已不再即時分享剛拍的植物,經常等花期過了才張貼照片,「算是幫植物避避風頭」。他也不解,如果真心對植物有所好奇、有所愛,為什麼會只想拍花,而對植物的整個生長過程毫不在意?
「有時候會在社團看到有人拍一系列的照片,從植物的幼株、葉子、花、果實……都有,就像經歷小朋友從小到大的過程,參與它的成長而不只是拿現成的,我覺得比較有意義,去學習、了解這些植物的形態,心裡也會比較踏實」。
就像來時路上,山野人不經意拐入了一條小徑,要我們下車觀賞一片圍籬栽有台灣少見的枸杞;又或海岸邊一路前行,他和張家昀經常駐足喚出路旁小草小花的名字,並娓娓訴說這些植物偏好的生長環境,或是東北角的族群長相和這裡的有何差異;說起促成兩人結為「植物聯盟」的列當,他們也如回憶老友行跡說著:從前羅東溪畔本也有一些列當,但前些年砂石車忽然開進溪岸,列當的家想當然爾不再留存,至今宜蘭他們也只在此地見過列當,其他地方都沒發現,聽說高山上有,但花期會比較晚,也許要到七八月了……
「去年我們是從停車的地方就看到列當,而且開得很多,今天大概是來得早了」,不過無妨,能親眼見到宛如小精靈般的列當本尊,這場尋寶記讓人切身感覺到與陌生植物建立關係的美好。
雨停了,一行人回到停車處,不知是誰指著後輪胎右側草叢大叫:「這裡怎麼有這麼大叢的列當!剛下車都沒發現!」和我們先前看到的植株不同,這叢列當家族已到花季末了,紫色花穗轉為熟成的棕,就像一束靜靜放妥的花束,等待人們驀然回首的發現。

※本文首次公開刊登於端傳媒〈幫植物避避風頭:民間高手如何保護台灣珍稀動物〉,202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