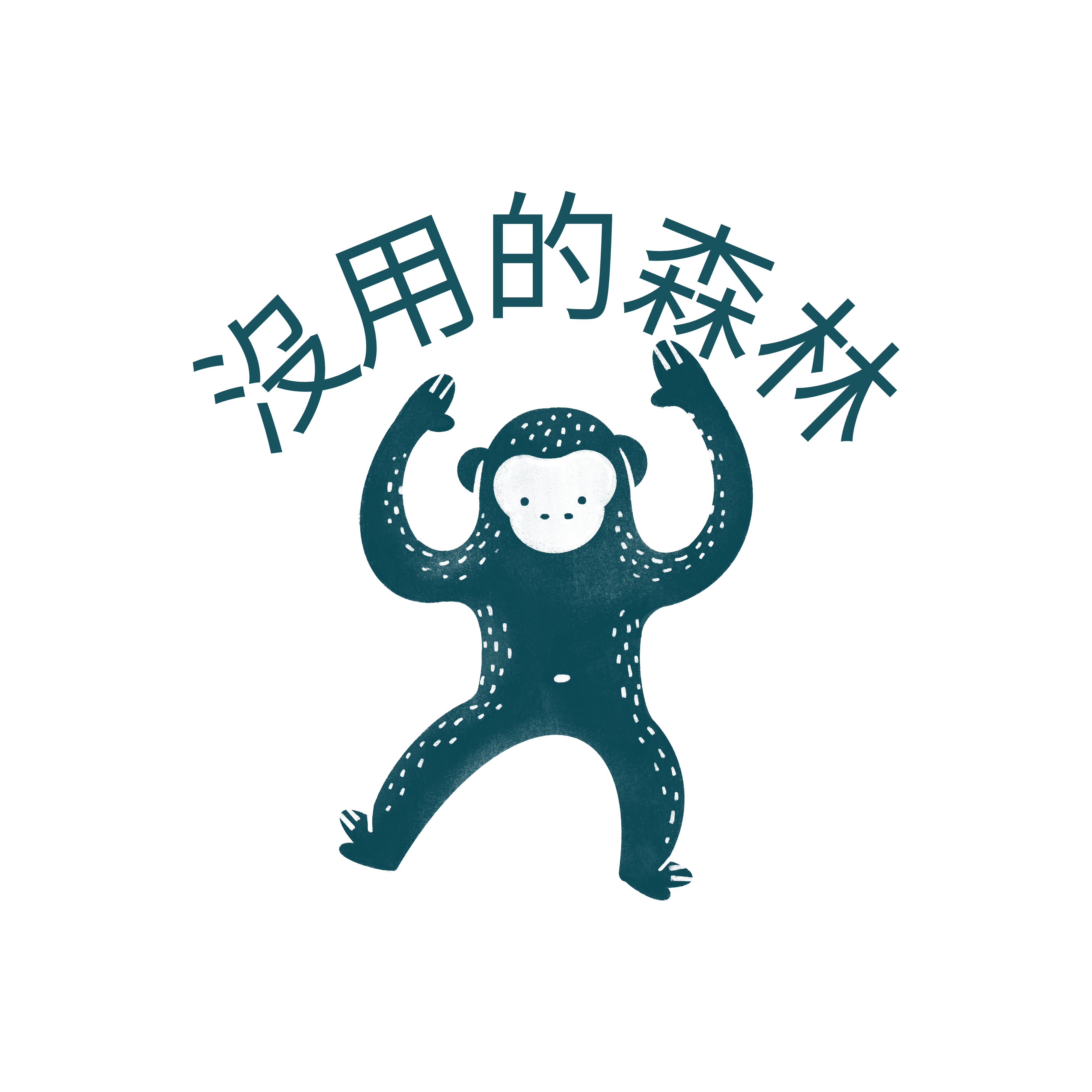第二次通電話時,余彥芳說,她正為即將養貓而焦慮。40歲的女性表演藝術家,未婚、未生,這是她第一次決定承擔另一個生命,雖然有伴侶一起,「我另一半對這件事相對穩定,但我是熱愛自由的水瓶耶!」貓一天不來,塵埃便無法落定,她的焦慮不斷增生——從此以後,她就要成為一個哪怕走到天涯海角,都得有所承擔、有所牽掛的人了。
天涯海角是早就去過的了。那時,余彥芳要承擔牽掛的,主要是自己的舞蹈生命。一個從小堅信自己能跳舞的女孩,求學期間的種種壓力挑剔,都沒能擊垮她的這份自信,舞步一路踩進美洲、歐洲、亞洲,不說橫衝直撞,至少理直氣壯。她形容當年的自己「根本沒在怕」,又說,「我很愛跳舞,世界上最愛跳舞的那群人,我就在那裡面」。學生時代一起跳舞的朋友,都說大概就她會一路跳到很老很老,無所謂封腳。如此堅定,近乎信仰,彷彿只要能跳舞,她的天空就不可能塌下來。
天空確實沒塌下來過,但是,穩穩支撐余彥芳跳舞的那塊地板,在她36歲那年,整片崩落。那是不可逆的崩落。從此以後,她成為一個不太一樣的人。一個依然愛跳舞,但不太一樣的余彥芳。
五月第一個禮拜,台灣仍可稱靜好。距離疫情引爆、全國三級警戒降臨,還有不到半個月。戴著口罩的觀眾排成長長序列走進廟旁的驫舞劇場。必須嚴格謹遵的社交距離和梅花座政策還未再臨,余彥芳站在門口,像個筵席主人似的把賓客一一接進座位。
那是哪個余彥芳?默默把自己安進「觀眾」身分的我,避開跟表演者互動的羞赧,迅速坐進中間位置,觀察起台前台側不停奔走的那人。放大的中壢客家口音、行走如揣摩一個比自己體型圓厚的男人、過分好客地把花生糖和汽水塞給賓客們……
這是一個在扮演別人的余彥芳。但她同時也跟幾個賓客以「彥芳老師」自稱。視來者和她平日的互動關係,這個表演者不斷穿戴不同的身分和對方招呼,但她的身體姿態一逕貼合著那個體型圓厚、咬字奇特的客家男人。
無論這是哪個余彥芳,我心中不無訝異地凝神觀看,都跟我認識的余彥芳不一樣。距離上次相見怕不只四年了。臉型未變,身形稍稍豐潤,但也只是一點。更何況,她在台上扮演。我說不出為什麼,但強烈感覺:眼前的余彥芳,和我過去認識的余彥芳,不是同一個人。
第一次見到余彥芳,也是相同的對應關係:我在台下,她在台上。那是2011年夏天,由周書毅策劃的第一屆「下一個編舞計畫」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上演。剛從美國返台的余彥芳是其中一位受邀創作的編舞者。多年過去,我的視覺印象始終鮮明:她穿著一件黑色馬甲式短洋裝,在裸露的工廠空間裡和牆壁、樑柱、地板、和自己跳舞。一片漆黑中,環繞她胸口的一顆愛心亮起霓虹光,讓她的獨舞成了一次非常刺眼、也非常鮮明的主張。
那支舞叫做《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多年後,當我為了寫這篇文章在網路上搜尋資料,才遲鈍地發現了這個巧合——余彥芳在驫舞劇場的演出,是為《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Ⅲ》。相隔十年,我看了同一位創作者的同名系列作品。
一樣名字的作品,在不同的時間流域中,探索的命題和提問者的精神內核會一樣嗎?
我在網路上找到一支影像,比現在年輕10歲的余彥芳在畫面中一字一句,清晰表述自己的創作意圖:「我可不可以不要做一個作品,是會完全佔領這個空間的?我不要你們所有人的注意力,有沒有可能?所以(觀眾能夠)從這裡去想像消失,想像不在,想像缺席,想像所有遞減的東西……」

「很多人跟我這樣講」,聽到我說在《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Ⅲ》看到她,感覺和從前的余彥芳不是同一個人,電話那頭的她發出一聲輕笑,「你覺得哪裡不一樣?」她反問。
具體來說,確實很多不一樣。通過疫情期間的線上電話,一問一答間,我們重新建構了過去沒聯繫也沒見面的四年,余彥芳怎麼被生活沖洗搓揉出另一種模樣。
首先,她成了「彥芳老師」,在原本的創作者和表演者之外,添加了教育者的身分。是三位一體,也是三分天下,雖然教學的比重變大,她認為自己仍以一個創作者的身分投入其中。她在臺北藝術大學和臺北市立大學教授創造性課程,遇上衝擊全世界的疫情,師生之間僅能以視訊鏡頭相繫,被舞蹈養成的眾人都不習慣身體被空間阻隔,但她告訴學生,無論生活藝術創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是Surrender(臣服),「你會anger,但當你surrender,也許能看到可以撿拾起來的事情,發現只有在這情況你才能感知到的東西」。
成為一個老師,她顯然樂在其中。在另一個為期四年的系列創作「默默計畫」將近尾聲時,余彥芳發現自己內在有強烈的「輸出」需求。從開始(2013)到結束(2017),「默默計畫」或許可以標記為余彥芳藝術創作的第二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她從美國學成返台,為了搞懂自己一度抵拒逃離的台灣舞蹈生態在負笈的這幾年變成什麼模樣,她迅速投入和不同舞團、劇團的合作。到了2013年,「默默」二字從一則新聞撞進了余彥芳眼皮,她號召了此前結識的一群創作夥伴,環繞這個疊字詞展開一連串探索。
「那時候我想要找一個表演藝術的最大值」,說罷余彥芳哈哈一笑,「那時候滿可愛……比較年輕,想要找獨特的身體、找說話的方式」,同時也為了一個更超越的企圖,「我想要處理一些更大的議題」。
那幾年,都市變更、土地開發、青年貧窮、兩岸政治……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在台灣捲起千堆雪,余彥芳和其他劇場工作者自然也投奔怒海之中,透過劇場裡外的行動和實踐,尋找改變的契機。然而,「就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你覺得事情可以被改變,你覺得你知道解法,就要當仁不讓衝到前面告訴大家什麼是對的,等到年紀大一點之後,哇嗚~世界沒那麼簡單喔~」年紀大一點的余彥芳對著當年的余彥芳苦笑,「作為一個人,如果我覺得做什麼事情就可以改變什麼,我真的是不成熟」。
承載著多樣宏大企圖的默默計畫,也因此遇上瓶頸。那段撞牆期發生在2017年余彥芳的36歲,往後她深深銘刻這個歲數這一年,因為發生太多失敗和失去。在最靠近創作心臟的層次,她認為自己的探索和企圖最終並未成功。不只如此,她還經歷了親人亡故、戀情結束的雙重失去。
「在那個失去跟失敗的過程中,你就是,被打趴到沒辦法接受自己了。就真的被打趴。於是過去的個性、逞強才能夠被化解,決定再也不用那些面貌去對任何人」。
到這裡,余彥芳決定自己回答這一題:
「你覺得余彥芳哪裡不一樣?」
「我覺得就是,我爸爸不見了。」
「我從來就是一個飛揚跋扈的人,從小到大都覺得,天塌下來也不會砸到我,因為有我爸媽。他們對待我的方式不一樣。我媽是會一邊抱著我一邊說『我女兒就是全世界最漂亮、最聰明、最幸運的女生』,這部份她非常美式,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就是很好地被催眠了。而我媽會說,我爸會做。我爸就是一個不閃耀的人,一個很普通的男人,可是他把我生活中的一切準備好。我的飛揚跋扈都是建立我爸的支撐上。」
「他生病十年,但做了化療,有七年他就像一般人一樣身體功能正常,胖胖的,看起來很健康。第八年又發現(癌細胞)了,就沒辦法。可是他到最後一次住院之前,都還是來載我。(我忍不住插嘴問她:像妳在《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Ⅲ》裡演的那樣,騎機車到中壢車站載妳?)對,但不是騎機車,改成開車。所以,一直到最後,我都感覺爸爸的支持沒有打太大折扣。」
「我爸過世後,我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是。我媽應該也是這樣覺得。我哥應該也是。我都跟別人說,有人形容爸媽死掉像是家裡柱子被抽掉,我的媽呀,我們家是我爸過世就像我家地板被抽掉,全家人開始往下掉,自由落體。」
「2017年那個過不完的36歲,滿想死的。那時我滿常去巴奈(設在二二八公園抗議原民傳統領域法令)的帳棚,遇到高俊宏,就問他上山能不能帶我去。第一次入山,裝備超級不齊全,路上好多坍方,又下雨,差點走不下來。回來後覺得生不如死,然後又約下一次。那時候就想要踩一些死亡的邊界,想要危險。」
「2019年(《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Ⅲ》首演當年)我是在一個從谷底慢慢爬回來、還沒有完全復原的情況下做這個作品。我試圖往死裡對證:我爸爸死了,為什麼我還活著?」
「2021年重演,是因為2019年演完那三場覺得不夠。這作品必須繼續演我才知道那是什麼。2021年是截然不同的狀態,但我還是經歷了情感勒索自己的過程,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那妳現在還有那麼想妳爸嗎?(沉默)很恐怖喔。非常恐怖。」
「重演是一個,情感上的考驗跟專業上的考驗。我花了大部分時間在適應我自己已然成為另一個人,已然跟我爸爸有截然不同的關係,但我爸爸仍是一個證明題:爸爸現在到底在哪裡?而專業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專業是你可以有條件、有成長地持續複製一個作品,它終究要離開一個『只是我跟我爸爸的關係』,要有另一個層次是『成為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今年有很多二刷的觀眾,他們的反應是:2019年看到爸爸,2021年看到女兒。這就是我的過程。又脫了一層皮,確認了這個作品可以繼續,也確認了其實爸爸給最多的,還是愛啦。我今天之所以有去跳最後一段舞蹈的力氣,有開闊跟對抗,都是因為有他。2019年是理智上知道,2021年更能用身體感知這件事情。」

2018年一月,即將37歲的余彥芳再次飛出去,去天涯海角的美國,那個讓她的藝術家心志開始萌芽的地方。還念大學時,她就清楚畢業後若留在臺灣,自己的藝術生涯不會長久,「直覺知道我得把自己養得夠壯才能再回來」。
她果然也被西方國家注重內在陶冶的教育滋養地飽滿強壯。當時遇到的恩師比比.米勒(Bebe Miller)展現的身教,直到現在還受用:「身為藝術家,你可以是個天才而不必是個混蛋」,「美國的藝術家那麼多,不只比比,我接觸到很多藝術家,他們的藝術追求跟人格提昇是同時的。他們有很好的理由為什麼做藝術。」
南西.史塔克.史密斯(Nancy Stark Smith,1952-2020)是她選擇在2018年投奔的另一位恩師。南西是馳名的接觸即興大師,2013年時曾來台參與由古名伸舞團主辦的國際愛跳舞即興節,當時余彥芳從她身上看見了自己從19歲起學習的接觸即興,還有更寬廣的可能性,終於,在彷彿過不完的36歲快要結束時,她去美國和南西上了三星期的課,「像是孫悟空終於被收服了」。從此,她臣服於接觸即興,視為一種值得終生研究的思想體系,遠超過一門舞蹈技巧。
在那之前,余彥芳常在創作和表演之餘從事教學工作,然一旦親炙南西巨大的能量後,她意識到創作和教學可以是同一件事,也有了迫切想成為一個老師的需求。她跟兩位夥伴,學戲劇的湖雅婷和學法律的邱美蘅共同把以創作演出為訴求的「默默計畫」轉型成教學為主的「默默工作坊」,接收所有年齡層和不限舞者的學生前來「共學」,「我們有永樂市場的員工、燈塔建築師、電腦工程師……歲數從十幾二十歲到六十出頭都有,都一起教」。
教的當然是接觸即興,但,技術是副產品,她想教育或說分享的,是接觸即興最重要的原則——當面對世界、社會、家庭,乃至另一個人,你能否在行動和互動中保有覺察和理解,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可能性?
「我一直都希望藝術的能量可以提昇人的生活品質」,余彥芳說。在勸慰因線上教學受挫的舞蹈系學生時,在回看那個經受各種失去和失落的自己時,她總是提起藝術,「我很感謝我的藝術教育,我感謝自己是個artist(藝術家)」。
她告訴學生,這段時間是「你作為藝術家最賺的時候,因為全世界都在失去,可是我們的教育是『你所有的經驗最後都會變成你的養分』——只有我們在持續地賺」,她哈哈大笑。
失去無可取代的父親,她告訴自己,無可取代也意味父親之於她有多重要,而這個領略,她形容為「我們作為artist的blessing(祝福)」,「我們的教育讓我們能夠理解這個不可取代性,讓我們接受很多事是獨一無二、無法取代的,以及隨失去而來的殘缺」。
Artist。不再是聽到人家叫「藝術家」就身體往後一縮的那個人,余彥芳現在會雙手一攤、肩膀一聳,「對啊,我是藝術家」,她從未決定、從未想要成為一個藝術家,然而她已然是一個藝術家,因為願意承擔種種隨名字而來的責任或使命——
作為一個藝術家,你的責任是,你不停揭露自己內裡如何想像,以及想像的過程。你將想像力釋放並昭示在別人面前,於是別人看了之後會想:也許我也能想像。
因為我以身作則地做了這件事,同時讓別人看見我是這樣活著的,以此作為反抗理所當然的工具。」
到此為止,我發現了一個和從前一樣的余彥芳。10年前,那個邀請觀眾「想像消失,想像不在,想像缺席,想像所有遞減的東西」的藝術家,在經驗種種想像化為真實的試煉後,依然確切相信想像的力量。
※本文首次刊登於 國藝會線上誌 2021.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