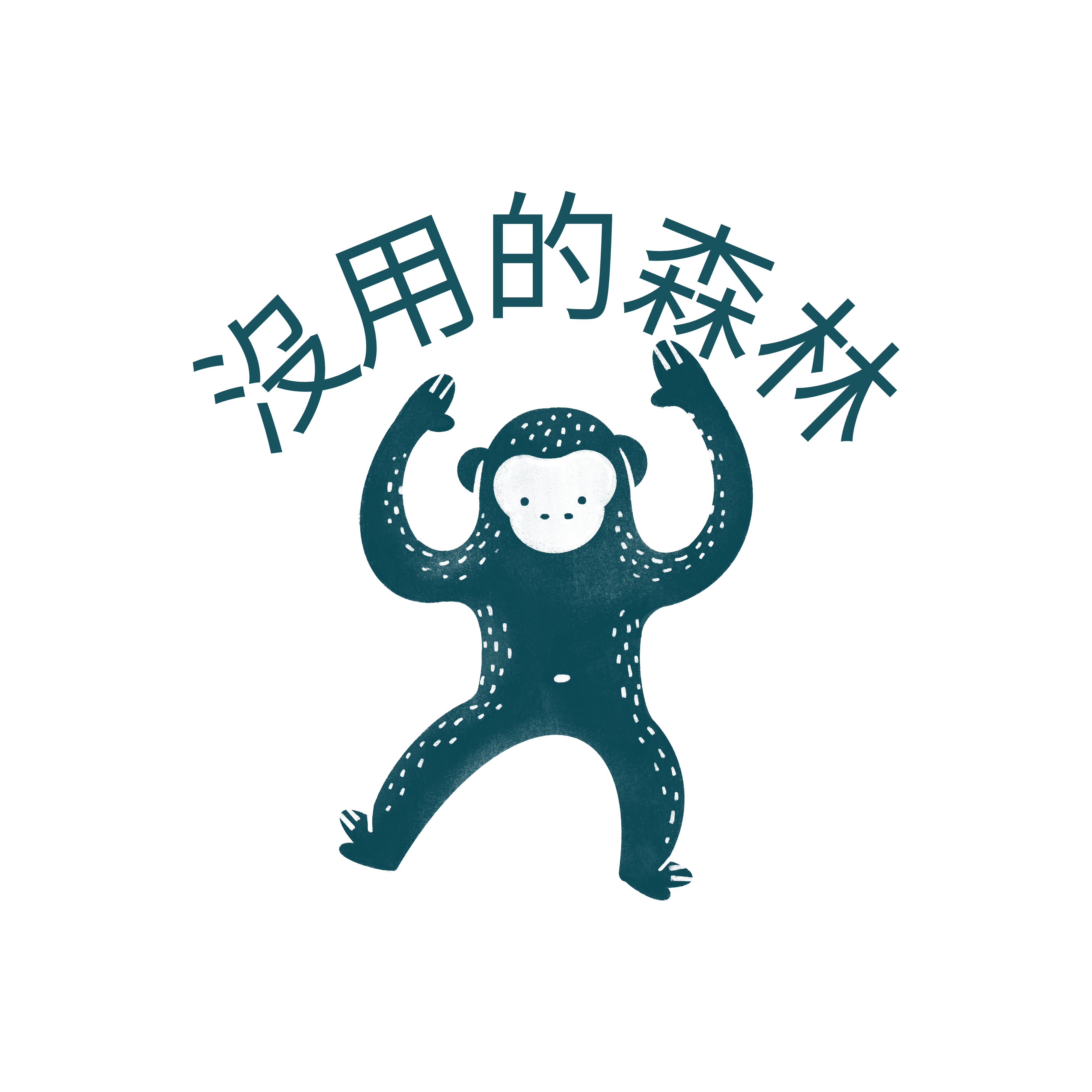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我們要活下去,凡尼亞舅舅,我們要日日夜夜無止盡的生活下去,我們要有耐心忍受命運對我們的裁判,我們要為別人工作,從現在到老,永遠沒有止息,當大限來時,我們心甘情願就死,躺在墳墓裡,我們會說,我們曾經受過苦,我們哭過,我們嚐盡了苦頭,老天會憐憫我們;你和我,舅舅,親愛的舅舅,我們會看到一個光明的、美麗的、美好的生命,我們會覺得很高興,到時候我們會用溫和的態度回頭看我們今天所受的苦難,然後一笑置之——我們會得到休息的,我有信心,舅舅,我有強烈熱絡的信心……」
沒記錯的話,這段台詞第一次出現時,是個哀愁的預感。妻子朗誦的桑妮亞在劇末的這一段台詞,被錄音帶平穩送進家福的耳中。他在車中愣愣著,還不知該如何面對早上出門前妻子那句「我有事想跟你談談」。
如果是村上春樹的書迷,聽到這樣的話大概心裡有數,妻子即將被小說家送去執行消失、離開,或「失去」的戲份,而被留下來的丈夫/僕/渡邊,則將踏上尋找的旅程。而家福面對的是,猝逝的妻子。失去了,且再無溝通或理解的可能。
或許是被那哀愁的預感捕捉了,或是人近中年萬一觸及契訶夫總是被撩動內心最容易動搖的部分,第一次聽到家福念誦這段獨白時,我就忍不住掉淚了。無可奈何地用力擺出笑,迎向前去。帶著妻子的死亡和對她的不可解,仍要日日夜夜無止盡生活下去的家福。
家福有過了解妻子的瞬間,用年輕演員高槻的說法,是對於另一個人,有些事情無論如何只能通過性才能了解。妻子像是《1Q84》的深繪里那樣,Reciever般出神騎在家福身上,喃喃吐露從幽黯深處浮出的八目鰻在海底吸附石頭的故事,家福躺在她身下,忽然像是不堪逼視深淵那樣,舉起手臂遮住自己的雙眼。不看。
高槻是因為沒有遮住雙眼,才得以知道更多嗎?那個過於仰賴直覺行動,在家福看來缺乏深度的他,毫不放過地盯著家福/鏡頭,說出了妻子告訴他的故事結尾。但這也並不表示愛的多寡或勝負。這不是什麼可以比較的東西。
雖然如此,就像村上說的,受傷了還是會流血(但出現的槍並不一定會射出子彈)。歷經各種尋找關卡的男主角,在村上春樹後期小說終於學會開口了。「對,我受傷了,而且非常深」,家福/木野對自己這樣說,然後流淚。
這也所以即使家福和年輕女子渡里必須迢迢從廣島開車到北海道,在雪地中流著眼淚說「我深深受傷了」看來有些刻意和出戲,身為觀眾的我仍不能就此批評些什麼。即使說得像台詞一樣,即使哭得像表演一樣,家福這個職業為演員的男人卻有必須掙扎著把這些話從嘴裡說出的必要。說出才能肯認自己的傷痛。而且絕不能是「冷讀」。也許是我過度解讀,但我覺得,這段戲從場景、語言到表演的「刻意」有其必要。
因為,若不如此,我們就無法全心全意感覺韓國瘖啞演員李尹秀飾演桑尼亞,抱著家福飾演的凡尼亞舅舅,用手語鏗鏘敲出的那段台詞有多麼是語言而又超越語言的力量了。她從背後攬住凡尼亞舅舅,用身體和手指把她與家福之間傳遞的那麼沉又那麼溫柔的能量對著台下的觀眾展開:
我們要活下去,凡尼亞舅舅
(這裡摘錄的劇本台詞出自劉森堯老師翻譯的桂冠版凡尼亞舅舅)
我們要日日夜夜無止盡的生活下去
我們要有耐心忍受命運對我們的裁判
我們要為別人工作,從現在到老,永遠沒有止息
當大限來時,我們心甘情願就死
躺在墳墓裡,我們會說
我們曾經受過苦,我們哭過,我們嚐盡了苦頭
老天會憐憫我們
你和我,舅舅,親愛的舅舅
我們會看到一個光明的、美麗的、美好的生命
我們會覺得很高興
到時候我們會用溫和的態度回頭看我們今天所受的苦難
然後一笑置之
我們會得到休息的
我有信心
舅舅
我有強烈熱絡的信心
謝謝濱口龍介,牽著我們的手走進村上春樹,在那裡找到了契訶夫,感謝濱口,把原作那句(過於年輕而)過度笨拙的來自渡里的安慰「那種東西就像病一樣。家福先生。多想也沒用。」換成了渡輪、撲天蓋地的雪、和李尹秀的桑尼亞。

而且諸君啊
西島以這個角色在日本金像獎打敗役所廣司哪!
諸君難道不好奇他的決勝一場是兜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