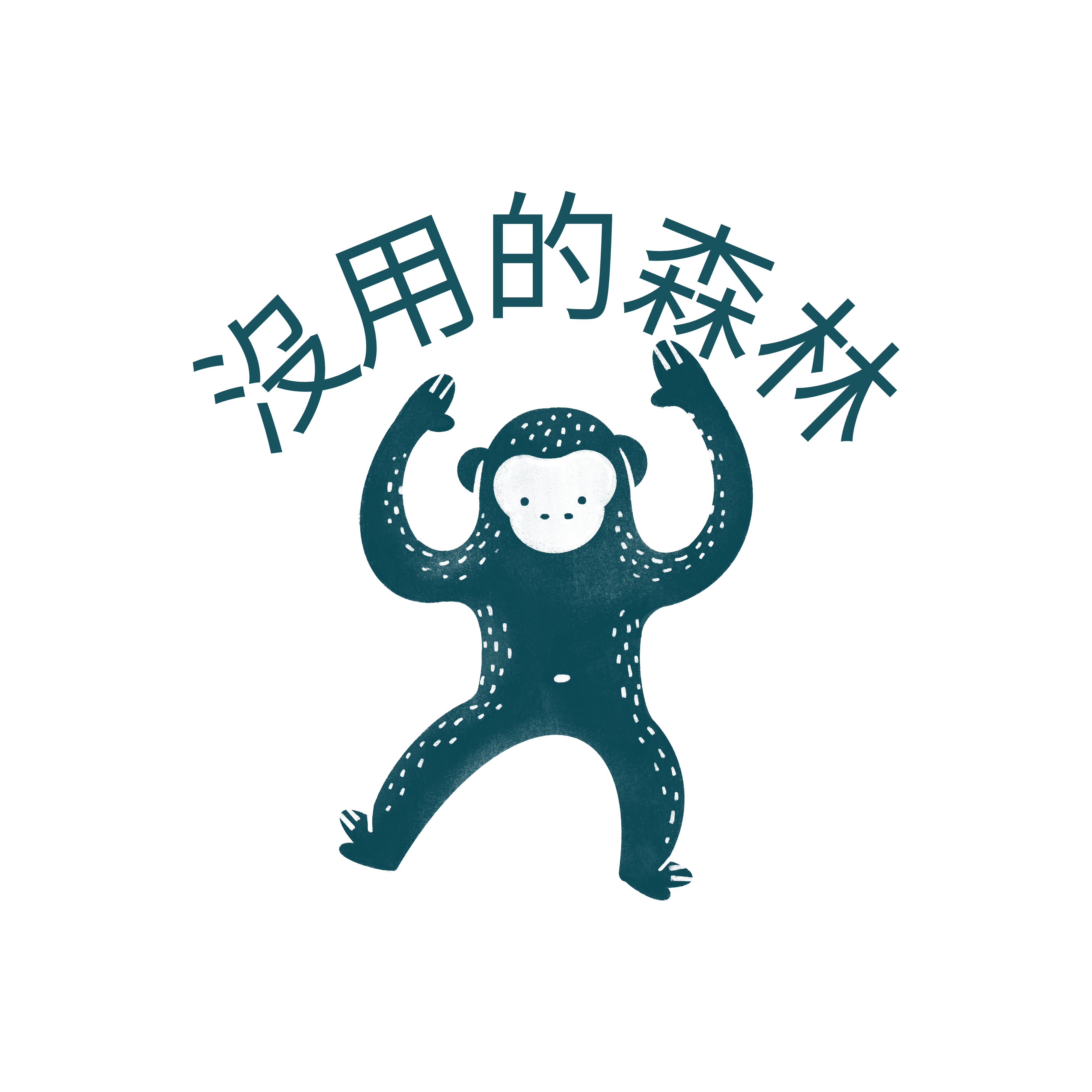阿米斯音樂節第二天傍晚,當鼎東客運把參加音樂節工作坊的最後一批遊客載走後,都蘭大街人潮褪去,只剩三兩小吃店家還開著,除此之外一片靜悄悄。唯有仍高懸於不少家戶門前的「阿米斯國旗」,見證過去兩天音樂節為都蘭帶來的狂歡和喧囂。
今年十一月五、六日在台東都蘭部落的阿米斯音樂節,是第三度舉辦。這個由都蘭明星、曾獲金曲獎與金馬獎的流行樂手舒米恩一手促成的音樂節,是東部少有的大型售票音樂節,標榜「沒有演出名單、沒有節目表」,逆反商業操作的模式卻成功引起矚目,今年甚至吸引多達兩千人次的遊客與部落居民參與。
無法預期的演出內容,且今年連知名樂團或歌手都付之闕如,為什麼阿米斯音樂節能吸引台灣各地,甚至來自港澳日本的外客前來?
音樂節結束後,我在都蘭繼續停留了三天。民宿老闆娘告訴我,她是第一天在都蘭國中操場上跳婦女舞的表演者之一,聽說我沒在傍晚和所有人一起跳舞,「很可惜耶妳,沒關係,下次再來玩!」
晚上,我到都蘭唯一的墨西哥餐廳老闆娘推薦我的小吃攤買阿米斯風味的月桃肉粽,本想問問他們在音樂節擺攤販售、造成大排長龍的烤魚有沒有賣剩的可讓我一嚐風味?「沒有囉!我們的魚都是自己養的,音樂節都賣光光,下次音樂節再來買……」
在都蘭國中遇到的青年,是音樂節升旗典禮後,跳著Malikoda(註1)為一系列表演揭開序幕的Pakarongay(註2),他們還沒從音樂節的狂歡和身體勞累中恢復,臉上卻帶著一絲自得的神情。位在都蘭國小前面的「32鄰咖啡」裡,服務生一邊煮咖啡一邊告訴我,她從附近的排灣族部落嫁過來,覺得音樂節是辦得好,但她更在意的是,「都蘭部落的凝聚力很強,我們部落沒有這樣,讓我很羨慕」。
阿米斯音樂節,是一個由部落集體參與、演出的文化展演。音樂節核心的歌舞表演由部落各Kaput(註3)的男女老少擔綱,擴散出去的活動包括符合「美式」風格—阿美族的美—的生活攤位,從原住民最廣為人知的烤山豬肉到阿美族工藝的藤編、毛線球、麻織網袋……一應俱全。這些攤主也多是音樂節第二天的手藝或傳統歌謠工作坊老師,提供不甘只是觀光客的遊人親炙阿美族文化的經驗。
這是舒米恩極力想跟族人證明的:即使不靠政府,部落也能設法找到自給自足的方式。
舒米恩不諱言,辦音樂節,是為了給族人帶來收入。這些年,原住民議題在「轉型正義」的潮流下,漸從邊緣滑入主流,認同的重新建構是重要的,然而,部落硬體設施的改善和興建,或是全台各部落對外開放的大小祭儀、歌舞表演,這些政府挹注支持的項目能對原住民部落帶來多少助益?
舒米恩的成長過程正經歷了原住民從備受歧視到漸獲重視的大環境轉變。他眼見部落恢復許久未辦的Pakarongay,因向政府申請補助而需要同時補習英文數學,壓縮了傳統技能的訓練;部落舉辦的豐年祭等活動也仰賴公部門補助,年齡階層卻往往為了幾千幾萬元該分配給哪些活動而屢起爭端,更別說年輕族人的教育總是第一個被犧牲。二○○八年,已成知名歌手的他開始自掏腰包,為弟弟妹妹辦起Pakarongay、海邊的孩子音樂會等活動,錢的問題也曾在講求資源共享的部落中引起質疑,長期以申請政府資源辦理部落活動的族人們也不明白:部落長期為貧困所苦,有資源就該珍惜,為什麼你舒米恩這麼堅持不拿公部門補助?
但這卻是舒米恩極力想和族人證明的:即使不靠政府,部落也能設法找到自給自足的方式。表面上,這是一道經濟的問題,舒米恩看見的卻是政府對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半調子支持。
就像早已辦遍全台灣大小部落的豐年祭,一台台遊覽車載送源源不絕的觀光客進到部落,外來攤位也紛紛爭一席之地,準備豐年祭表演的族人不僅無法從中獲取收入,還不斷被觀光客質問:「什麼時候要跳舞給我們看?」
「豐年祭就像漢人吃年夜飯,是重要的儀式,人家吃年夜飯,你怎麼會跑進來鬧?」一年一年過去,由於豐年祭是最符合外人對原住民刻板印象的文化活動之一,多能獲取公家補助,然而,豐年祭的精神意涵和文化性,就這麼被觀光行為模糊了本來面貌。
我問舒米恩,阿米斯音樂節開幕時,也有族人在操場上由內而外圍成螺旋跳舞,跟豐年祭歌舞給人的印象相仿?「不,那是不一樣的。豐年祭的歌舞儀式性更強。我們想呈現的是文化的性格跟倫理,而透過Malikoda這樣的舞蹈形式最容易表現出來」,他解釋,Kaput年齡階層的意義就存在於歌舞中,例如上場的順序,是依照長幼有序的邏輯,因此,這樣的歌舞並不強調儀式性,而是部落組織結構和倫理的具象展現。
我想起同時間在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展出的「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敘事」,小小的展間裡,呈現十多位都蘭族人的口述資料與文物,而展場設計也是仿照豐年祭舞圈的螺旋狀階序順序,將每個參展人在舞圈中的位置作為現場展現個人生命史的位置。族人在儀式歌舞中的「現身」,對應著自身在部落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個體與群體的關係無需複雜言說,歌舞陣式已說明一切。
年輕人就活在當代。他們有更多機會認識世界,找到當代方法,把知識帶回生活中。
像這樣的例子,穿插在音樂節的大小環節中。表演活動的安排設計細心蘊藏文化展演和認同的主題,都是舒米恩透過長年部落活動的經驗,以及親自觀察國際音樂節後,為都蘭部落重新量身打造而成。
「阿米斯音樂節有兩個原型,一個是沖繩國際音樂節,一個是鹿兒島音樂節」,舒米恩說,沖繩國際音樂節中有個舞台專供沖繩音樂表演者演出,從傳統三味線到跨界的搖滾、電子都有,「非常沖繩的舞台,當一個好奇沖繩文化的外國人來看,就會選擇這個」;鹿兒島音樂節則以社區居民親自擔任素人表演者聞名,音樂節攤位也全是在地特產,社區動員的能量強大,地域特色又濃烈,這兩者,都蘭恰好都有。
舒米恩羨慕沖繩能用音樂節宣揚文化,「當地政府也用沖繩意象宣揚自己。台灣政府就很複雜,一下用客家、一下用閩南,用阿美族不公平,下次就用排灣族、泰雅族……很錯亂,一切只為公平,做起來就四不像,某種程度,政府變成幫倒忙」。
然而,作為一種文化展演,除了傳統歌舞和年齡階層外,阿米斯音樂節還需要端出怎樣的菜色,才具備「非常都蘭」的意象?
「我不想太強調傳統的部分」,舒米恩說。阿美族固然有許多傳統文化與知識技能,但是,當人們過起現代生活,「吃肉不打獵,吃魚不射魚,那麼過去的生態、氣候、地形知識,什麼季節在什麼地方有什麼樣的魚,抓到魚後要跟什麼樣的香料一起煮,哪些魚給老人吃、哪些給小孩吃……打一條魚就有這麼多的生態知識和食物倫理,但當我們都去菜市場買菜,這些知識不再被應用,我們怎樣為這些知識找到當代的應用方法?」
他的答案一如既往。當年舒米恩決定將資源投注在部落年輕一代的Pakarongay,因為下一代才是未來,「年輕人就活在當代。他們有更多機會認識世界,找到當代方法,把知識帶回生活中」。
在孩子身上,異質表演和原住民性格的融合,正是當代生活與傳統感覺交會的最佳範例。
入夜後的阿米斯音樂節,操場上的節目隨夜幕降臨而告尾聲,人潮慢慢湧入從暱稱為「都蘭小巨蛋」的都蘭國中活動中心內。
這個音樂節主場,從下午就有青年樂團輪番登台。這些青年多是舒米恩在二○○七年時,以「海邊的孩子」音樂節之名訓練的弟弟妹妹,他們跟著舒米恩學樂器、練團、登台,其中幾個從孩童到大學生,從素人表演者到自組樂團,一步步踏上音樂之路,在故鄉的小巨蛋唱自己的歌。
夜晚的小巨蛋演出,更是驚奇連連。我的一位朋友,來自德國的戲劇工作者雷思遠趁著週末假期離開台北,到台東認識原住民文化。站在小巨蛋由籃球場搖身變成的觀眾席中,他一面興致盎然地看著台上演出,一面好奇問道,為什麼主辦單位會選擇在晚間最熱門的演出時段,安排一群青少年上台表演?演出內容且不拘音樂,從街舞、戲劇、國標、體操……海納百川地呈現?
「但你覺得有趣嗎?」我問,他熱切點頭,直稱自己沒來錯。從以自製樂器演奏阿美族傳統歌謠的旮亙樂團,重金屬風結合原民傳統舞的漂流出口,到眼下神情認真的各式孩童表演,他驚訝於原住民表演可以混搭跨界地這麼自由而多元。即使是業餘樂手、唱著口水歌的「搖滾媽媽」,他們在台上盡情享受演奏的模樣,也很能吸引觀眾一同投入。
「今年主要想做的是『童趣』」,舒米恩說,這是阿米斯首度以主題策劃音樂節內容,他刻意把孩子通通擺上台,「不管打鼓、跳國標、體操,就是要讓他們被看到」,因為,「再怎麼陌生的文化,只要通過小朋友就很容易感受」。
舒米恩解釋,孩子們的跨界表演是最有說服力的,他們像一張白紙,很自然地融入到不同的表演中,但依然保有很自己的、原住民的感覺。在孩子身上,異質表演和原住民性格的融合,正是當代生活與傳統感覺交會的最佳範例。
我們想立一面旗子在自己的土地,讓信心在自己土地上長起來。
除了部落裡的族人之外,舒米恩今年也首度「聯外」,邀請外客登上都蘭小巨蛋舞台,包括排灣族編舞家布拉瑞揚的《漂亮漂亮》,以及遠從沖繩來的讀谷村渡慶次青年會傳統舞表演。之所以有此初嘗試,是因舒米恩在參加關島南太平洋文化藝術節時,對他們集結南島語族文化共同呈現的印象深刻,「如果我們也邀請其他部落青年,或是一樣有年齡階層的部落交流演出,針對部落發展、文化觀光等議題集思廣益,或許會有更多新火花」。
事實上,無論南島語諸族或是沖繩民族,都與台灣原住民擁有相仿的命運、面臨的當代問題亦相似:殖民後歷史文化的流失與重建、觀光產業帶來的衝擊、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推廣、與國內其他民族如何共生共存……在這些複雜交錯的當代情境中,「認同」成了探討各種問題前首先要面對的,那麼,一場阿米斯音樂節能為都蘭部落累積出怎樣的認同?
在部落社區中漫步,每走幾步就會看見迎風飄揚的阿米斯旗。這面旗幟是今年初次登場,上頭的八角旗圖像源自阿美族傳統十字繡,原始紋路和意象繁複,舒米恩開玩笑說,旗上的圖案比較精簡,但老人家眼睛不好,就接受了。
會有這面旗,是因為想「升旗」。「第一、二屆時,我們一直在找音樂節的標的物,什麼能代表原住民?於是我們就想立一面旗子在自己的土地,讓信心在自己土地上長起來」,有了旗子,不如音樂節的開始就唱升旗歌吧!部落年輕人們討論後,決定要唱「都蘭歌」。
有旗,有歌,國家賦予人民投射認同的兩條件已具備。這也讓人想到八月時,蔡英文總統剛宣布選定都蘭為原住民自治試辦區域。我問舒米恩,他對自治的想像是什麼?
「就是在家裡的生活,能夠自己管理」。他說,部落在面臨政府治理時最大的問題,是傳統方式不被承認。「我們的Kaput不被政府承認,所以有很多機構必須成立法人才被承認,但明明我們就有拉中橋、拉監察、拉千禧等階層在管理部落的公共事務」,「如果我們能有自己的法,要做教育、要怎麼生活,一切都能合理」。
無論是舒米恩的「自己的家自己管理」,或其他自治區倡議者提出的「部落即城邦」或「國與國關係」,事實上,原住民自治議題在一九八七年由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正式提出後,歷經近三十年仍有許多疑義與施行上的難題待解。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對原住民正式道歉,儘管不夠誠意的批評聲浪巨大,卻總是引起更多公民針對原住民議題投以更多關注、進行更多細緻討論的機會。
我問舒米恩,音樂節開始時,那首都蘭歌到底唱什麼?
「那些歌外人聽起來都一樣吧?那也是應該的」,他露出淡淡的笑容,「這首歌是平常唱的,開頭唱出’Atolan,都蘭的名字,接著唱都蘭的人是什麼樣的人,男生下海,女生種田,我們是很勤勞的人……」
於是認同就從這裡開始。對陌生人唱著一代代Ina(註4)和Ama(註5)所傳唱的歌,用歌告訴人們,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處,我們現在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註1)Malikoda,台灣東岸阿美族豐年祭歌舞的統稱。
(註2)Pakarongay,約12-16歲的阿美族青少年階層,須接受其他年長階層給予的傳統知識、技能等訓練。
(註3)Kaput,阿美族「年齡階層」之意。青年以上的男性族人以五年(但不限於五年)為區隔形成階層組織,成年後須擔負管理部落公共事務等任務。
(註4)Ina,阿美族語,稱母親。
(註5)Ama,阿美族語,稱父親。
續讀相關文章:走進阿米斯日常—舒米恩帶你遊都蘭
※本文首次公開刊登於 2016年12月19日 端傳媒 〈旗飄揚、歌高唱:阿米斯音樂節如何形塑都蘭的部落認同〉
※ CC授權圖片來源:Bahamut C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