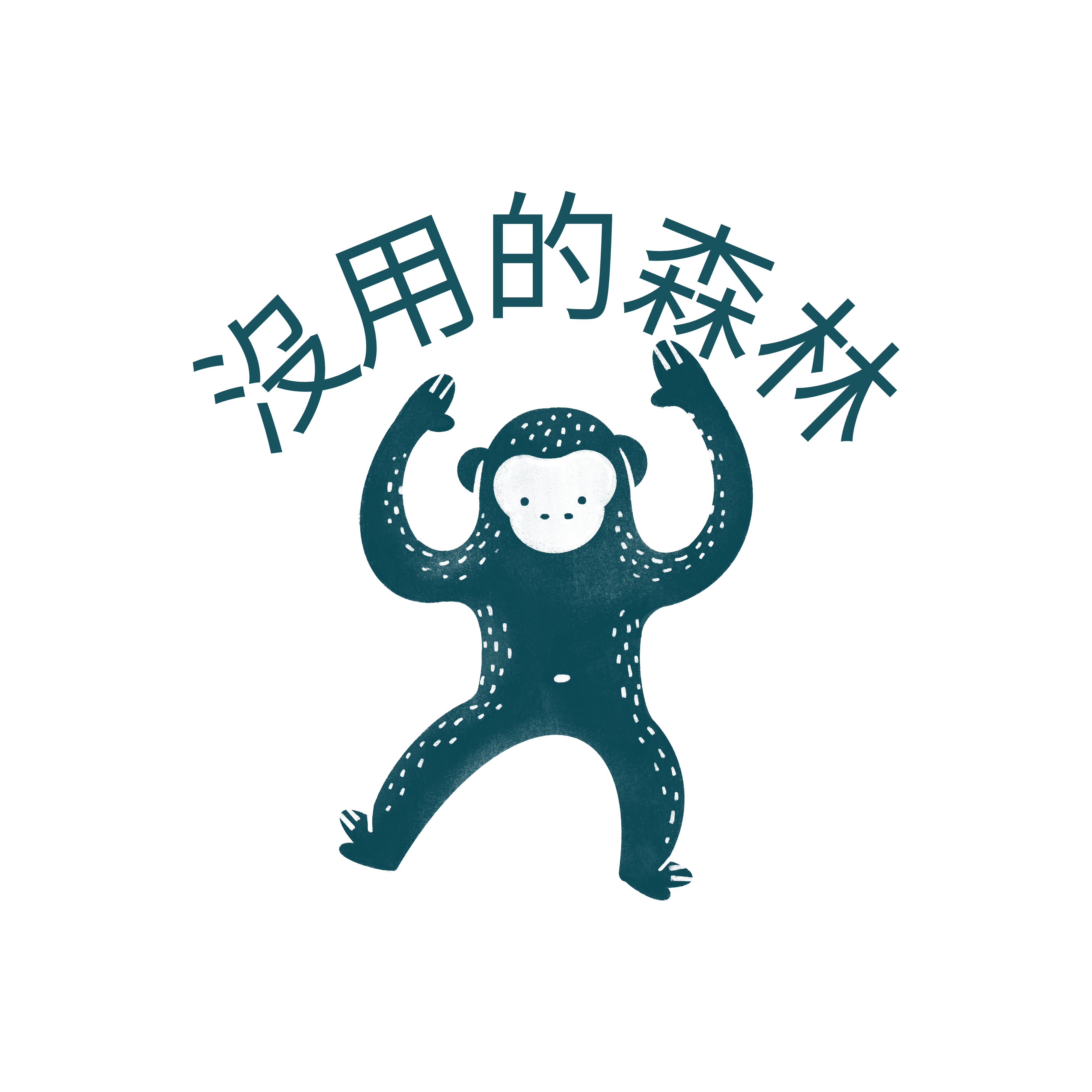抽空去了一趟戶政事務所,申請日本時代母系家族的戶籍謄本。
一天跑了兩趟。第一趟近中午,辦事人員說要午休了,這個資料的量非常大,能不能過中午再來?我沒問題。
第二趟特意延遲些時間去,但還是待了快一小時。辦事員一面嘮叨這種日本時代謄本特別麻煩,一面倒仍熱心地回答我問題:
「妳只能拿直系血親的資料,不能整個家族都拿。」
「妳要有生有死的,還是其他?有生有死就是要拜祖先的,妳不是?妳要寫什麼?寫祖譜嗎?那也要有生有死的啊!」
「有生有死就是你阿公阿嬤的出生跟死亡紀錄都在上面,還有妳阿公的爸爸媽媽,還有他們的爸爸媽媽……」
「妳只要看種族?都是『福』啦!福建的福。沒有『熟』。那妳還要不要有生有死?要我一起整理給妳。」
我有一點惆悵。起先是誰告訴我的呢?是TAI身體劇場的以新。是以新跟我說,如果好奇祖先有沒有原住民血統,可以去查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當時上頭會註記「生」、「熟」,意思是生番熟番。熟番多為後來的平埔,既然我懷疑,是有地方可查的。
懷疑的起點,是那回去柬埔寨。我不明白怎麼一下飛機觸目所及的當地人,眉眼輪廓像極了我外婆家那邊的幾個親戚。後來才知道「南島語族」二字。
跟媽媽聊天時我刻意問起這事。記得外婆出嫁前的家在高雄田寮山上。山區,還有外婆那張黝黑的臉龐,還有那幾個親戚深邃的輪廓跟黧黑的皮膚,其中一個從小外號叫「山地人」。這就是我所有的稀薄的線索。
可是現在戶籍謄本上清清楚楚的寫著:福。即使無論我外婆還是外公的家族,日本時代的現住所都註記著「番地」二字。這倒是沒錯的,在我能自行尋找的資料中,田寮和阿蓮都曾是平埔族的聚落,阿蓮這個地名的起源,有一說就來自平埔。
但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其他謄本裡的訊息帶走:原來,經由謄本我可以溯及六代的祖先姓名。我能知道他們各自是家族中排序第幾的孩子,在父母幾歲時出生,父母何時締結婚姻,又在人間活了多少歲數。有人纏足。有人接種天花疫苗。男人多務農。女子多理家或名為無職。有人招贅。有人壯年隕落。有人生卒不詳。生卒不詳的那個我聽外婆說過。那是一個沒能從南洋戰場回來的男人。是她的父親。那是個漢人嗎?她的母親,那個名字有好幾個「止」字的女人成了戶長,在那之前之後落戶番地好幾代的他們,有沒有可能只是名義上的「福」?
我被那一長串的名字誘惑著。如果繼續往六代以前無止盡地回溯,最終出現在系譜上的,會是一頭豹還是一枚海中的藻?
這些漫無邊際的想像夾雜著辦事員忍不住脫口的「光弄這批就弄了兩小時」。我抬頭,右邊有個老先生被一男一女推著輪椅前來,說要辦印鑑證明。老先生連自己的名字都說不全,戶政人員委婉建議那對男女尋求法律協助更穩妥。左邊一對伴侶來拿結婚登記資料,其中一位是一望即知的跨性別。
我想起稍早在醫院填寫的資料,要我追溯家族重大疾病史。能想的起來只有我從未見過的外公,從戶籍謄本上可以清楚對照,他是家族中少數壯年就因病過世的人。我那些高壽的祖先們,默默地活,默默地死,「因老衰在本藉地死亡」。沒想到,歷史終究留下他們一筆。沒想到,我會在這裡與他們相遇。
辦事員花了兩小時印出的一疊資料,我只被允許拿回其中幾張,120元。我家族第一塊拼圖的價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