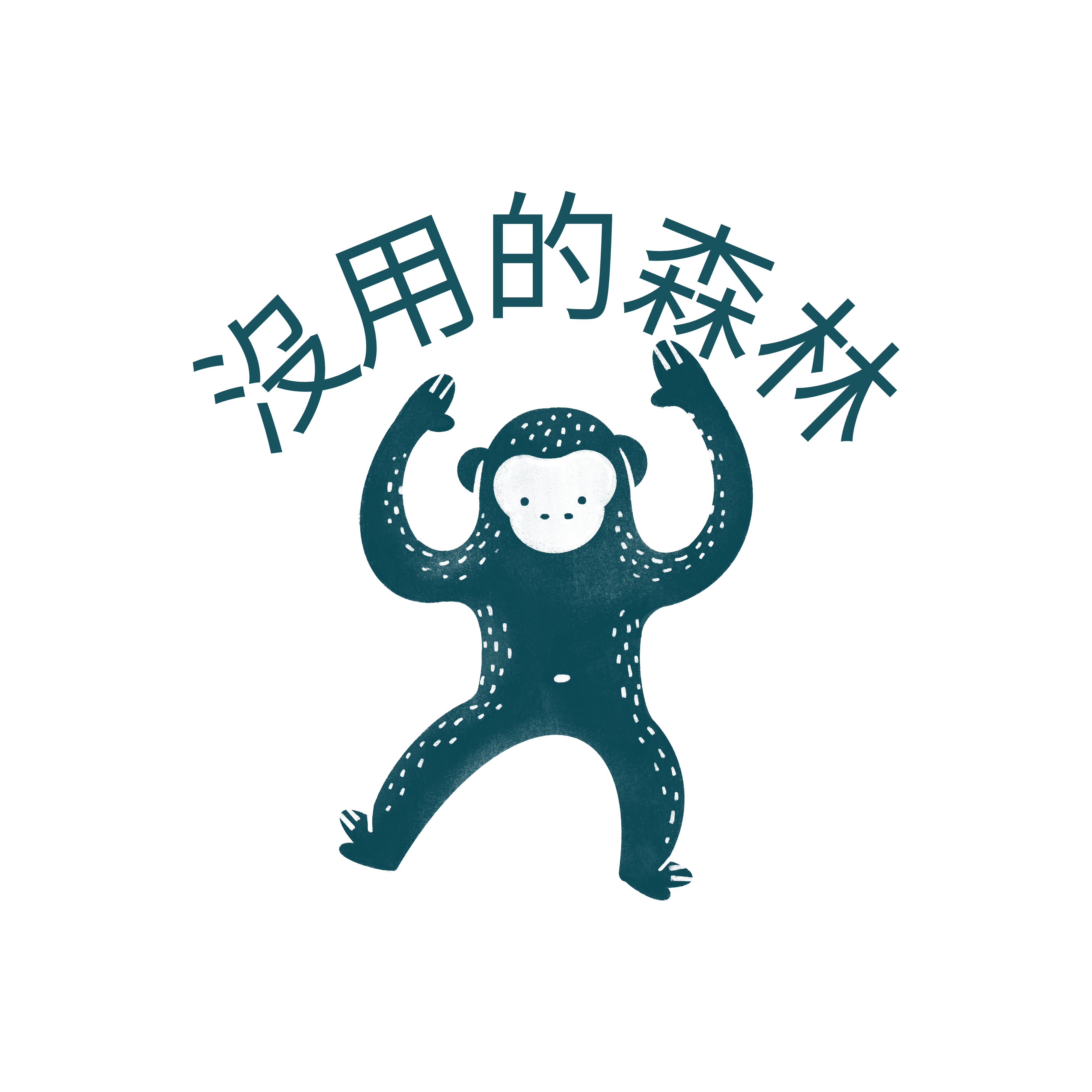在山路上,她問我:我登山的目標是什麼?
那是陽明山大縱走東段半途,過了適合休憩午餐的柳杉林,但離擎天崗大草原為時尚久的一段平緩路段。夾道的灌木叢如果沒記錯,是早過了花季的金毛杜鵑,因而我們步履不曾為賞花停下。它們成了凸顯我們輕快腳程的滯重背景。
我沒有目標欸,在腦海中巡邏半晌後,我(不無驚訝地)回答她。嚴格來說,不是沒有目標,是沒有能大方宣布的目標。珠穆朗瑪、K2、阿爾卑斯、台灣百岳、中央山脈大縱走……這些台灣山人的「此生必去」,我幾乎全無慾望。
開什麼玩笑,我可是連台灣第一高峰玉山都還沒去過的登山客。
我沒有登山的目標,但我有一幅勾勒好草稿的登山自畫像。場景不必名山,也不需大開大闔的風雲際會;那些會搞得爬山者一身狼狽、血淚汗水與蚊蟲水蛭咬痕交織的中級山或許更適切。我希望的畫像是這樣:即使獨自一人入山,即使要在山中度過幾夜,也能一身狼狽,帶著血、淚、汗水與傷痕,完整下山的人。
說也奇怪,明明架上不少登山經典,我卻很少被登山家的冒險故事征服。動念登山後首先翻讀的,也不是如何購置裝備或規畫路線,而是山野奇談。或許典型的登山經驗在我心底未曾離開「獵奇」的標籤列,僅供參考而不必親臨。
這種幽微的叛逆,在讀到「並不是因為山在那裡,所以才去登山」時,很有一口悶氣痛快吁出之感。句子是日本小說家湊佳苗寫的。短篇小說集《山女日記》開篇那個初次登山就不得不跟討厭的人結伴的女子,隨口就推翻掉馬勒里的名言,也道出這時代登山者(包含大量山女子)那不算嶄新卻更厚重的驅動力:「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幾乎看不到山,必須搭乘交通工具前往山區,才能夠登山。」
我不知道別人,但我經常為了逃開日常生活而往山走去。但妳當然不可能毫無罣礙的完成逃避行動,所以會遇到跟討厭的人一起爬山,且比在山下更痛苦地24小時與對方全天候相伴。明知平日戴上各種意義的面具疲憊透頂,卻也無法一支眉筆也不帶、一點隔離霜也不上的和心儀對象上山去。想任性地獨攀登頂,偏偏遇上仰賴妳支持陪伴的弱者。巴不得用輕快靈活的登山姿態抹掉別人對妳山下又宅又魯的失敗者形象,可是攻頂下山後,妳依然要變回那個坐困愁城的徒勞者……《山女日記》中一面又一面折射鏡,讓我所有微妙的登山動力都現形,雖然有點難堪,但也不是沒有安慰。
安慰,來自於小說裡的每個她,不管有意識無意識,都迫切地想找到自己登山的節奏,「不能按照自己的節奏登山最累人了。」雖然山路與平路一樣,總有狹路相逢時,而我知道好幾個登山女子,寧可在隊伍後頭慢慢走,換取用自己的步調跟山所掩蓋的一切對決,或和解。
這樣的呼聲,漫畫《山與食欲與我》的女主角也經常發自內心喊出。這是一個體力與能力俱佳,乾脆以「單獨登山女子」區隔自己,好換取最大自由的登山者。在台灣不管有沒有開放山域,始終糾結於獨攀的安全性和公共性問題之際,27歲的日日野鮎美早就背起15公斤重裝,獨自走進日本群山裡。沒有任何微言大義,也不是為了思考什麼抽象高深的人生哲理,只是想痛快地在山上走到全身大汗淋漓,接著給自己煮一頓美味的料理,安安靜靜地吃完,然後下山。像她這樣的登山者,在群體壓迫力十足的日本社會裡也並不孤單。如果把場景推往更廣義的自然戶外,漫畫《搖曳露營》和戲劇《一個人露營吃飽就睡》裡所要標舉的,都是這種孤身走向野外、在獨處中歇息的珍貴。
而這樣的一個人,走向山裡也不是為了完成什麼壯舉。不如說有一部分的登山,就是為了抹消「偉大」。
我始終難忘第一次爬到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奇萊南峰途中,一片廣遼的箭竹草原在眼前無限展開的模樣。強風不時尖嘯。當然感覺渺小,可是沒有畏懼,而是慰藉。想到這片地上有機無機的存在,從過去到現在都會繼續存在下去,而我這個過客只是它們的一瞬,我不知為何心存感激。哪怕接近永恆的不是我,而是它們。幸好是它們。
這樣的慰藉之感也陪著我一路走到南湖下圈谷的那段碎石路以及,閱讀整本《山之生》的過程。娜恩.雪柏德無數次入山,入的都是蘇格蘭高地同一座凱恩戈姆山。在她的書面世前還遠遠不是名山的凱恩戈姆,但雪柏德一次又一次攀登它,返回它。在凱恩戈姆裡,她跟登山,跟自己的身體,締結了一種獨一無二的關係。她寫石楠、金鵰、牡鹿、雨燕,像熟之不能再熟的鄰人知己,隨便拾取的記憶都有新奇的發現。她和科學家上山學習辨識生物,但山最終仍對她揭露:知識不會驅散生命的奧祕。她寫風、寫岩、寫霧,寫湖泊和霜雪,沒有焦點,處處細節,但她不說偉大也不過分推崇,而是大地有「看待自己的方式」。
不只看待自己,山也看著我。那目光不帶愛物欲,也沒有威脅生命的張力,是一種冷靜的包容。我不太知道如何形容被那樣照看的感覺,但我拒絕承認那是長途跋涉在暗夜山路中的幻覺。雪柏德用她一生和凱恩戈姆深交的故事告訴我:所有我在山裡有過的感覺和經驗,可能會一起在生命盡頭處凝視我。那時我或將知道,關於我所描繪的這幅登山者的自畫像,最終是什麼模樣。
(首次公開刊載於新北市政府文化季刊202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