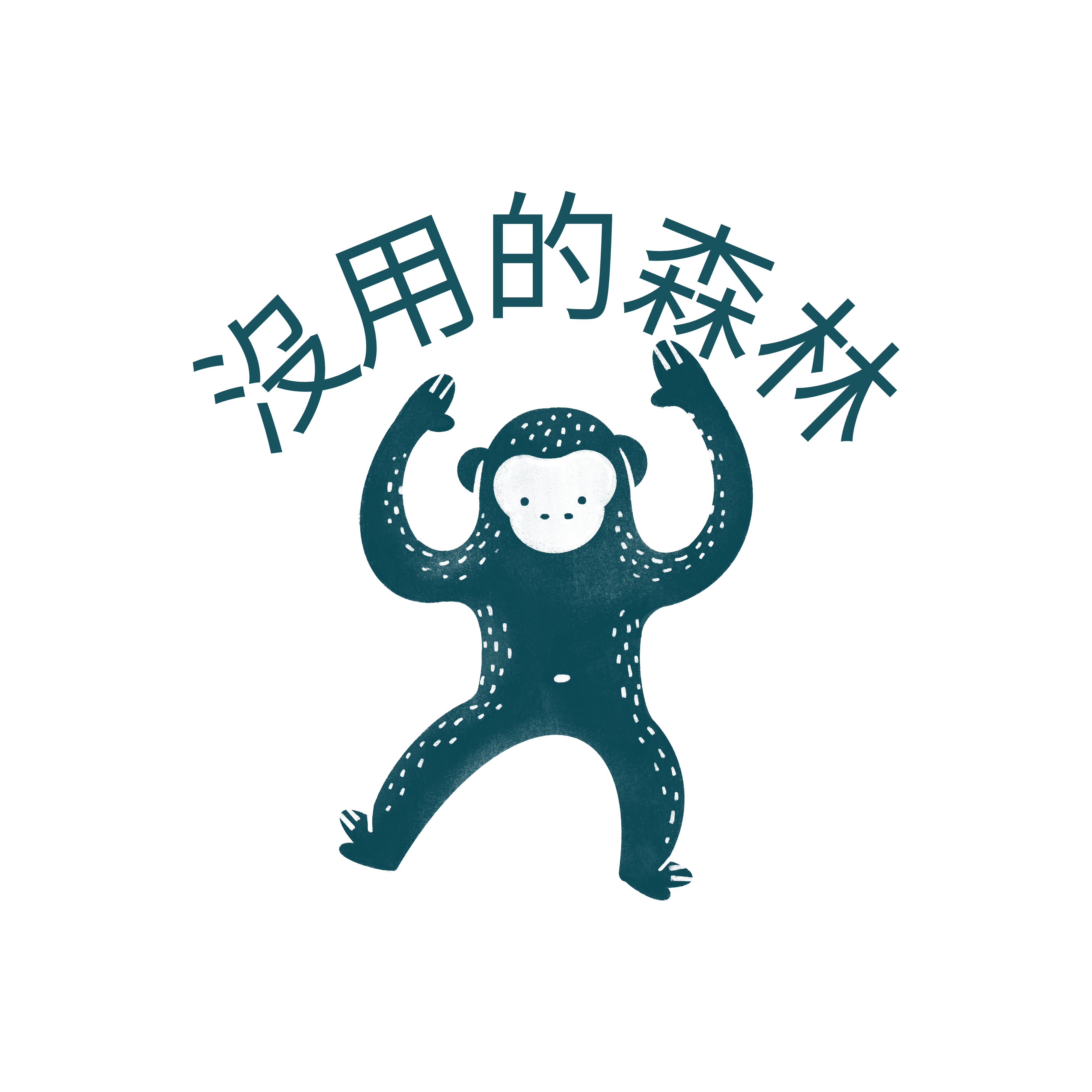我家窗外有座山。山不高,海拔不過一百公尺,典型的淺山。構成淺山地景的雜樹林,自我們大樓後方凹地往山坡蔓延。兩年來,我經常憑窗觀望這片淺山坡地,和我的心情思緒一樣,每日每時,它總在變化。
第一年的凹地上覆滿蕨類和我不認得的草本灌叢。入厝逢春天,夜復一夜,眾蛙合鳴,來探望客宿的妹妹徹夜未眠,才知道蛙鳴能安住我在城市焦慮慣了的身體放鬆沉睡。當初還是小苗的構樹,如今高逾三樓。芒草和大花咸豐草取代蕨類草本成為凹地主角。芭蕉枯黃。龍眼開花。群蛙沉寂。我終於說服自己走進這片每日觀望的風景裡,探勘究竟。
那日中午陰鬱無風,我換上壓縮褲,短袖羊毛排汗衣,防風外套鴨舌帽,把登山用的離線地圖APP點出來,確認這座淺山有數條明顯路徑可上稜線,但沒有一條能銜接我家後面的凹地。我打開GPS記錄行程,在隨身小包裡放進一片行動糧、一條曼陀珠,裝滿一壺水。猶豫片刻,我把登山用上層雨衣塞進袋中。這樣判斷:即便迷途,我應該有能力在日落前找到路回返,但萬一發生萬一,這些裝備應該足以抵禦一晚。
想到這裡,我忍不住想到那些在山難新聞底下留言謾罵的人——真的,一點都不是你們想的那樣,爬山是莽勇冒死之人的任性。每一次爬山,哪怕只是我家後面海拔百公尺的山,我都帶著怕死的心前去。
對爬山的第一個講究是:
我要活著回來。
起先,我依循離線地圖,往我家隔壁幾條巷子走去。圖上的巷末有路,可繞向我家後方,再迂迴上切至稜線。但這條路很快被掐斷了。私有土地,鐵柵深鎖,看門狗朝我猛吠。為什麼我不帶登山杖呢?平常喜歡狗,但此刻對牠們的氣燄簡直反感。
最後還是走回家門口,沒想到社區矮牆旁有條泥土小路可通往我日日俯望的凹地。從五樓看去低矮又平凡的草地,其實有我膝蓋高。因為無人,路徑全得靠我自己踩出。一股緊張感從我的胃糾結浮出,我再次自問:為什麼不帶登山杖呢?打草驚蛇四字,如今只能是我腦中的幻想。
理論上這季節還不至於有蛇。這般自我安慰,立刻被前幾天朋友爬山拍到的赤尾青竹絲照片湮滅。我把腳步放慢放重,避開凹地中央超過身高的芒草叢,往我自小看它長大的那棵構樹走去。構樹後頭露出一條泥徑,我攀住泥徑下方一叢粗壯桂竹,小心踩住一截腐朽但應可借力使力越過的竹幹,曲身跨到土徑上。一站直身子,就看見幾支空寶特瓶,和一座剛清理過的墳墓。
應該為死人畏懼的。應該為垃圾不滿的。但真正湧出的情緒是感激:有人跡就能放心前進。我一邊默念不好意思打擾了,一邊笑自己:你完全不是一塊冒險家的料子耶。別人爬山,往百岳爬,往大山爬,往未有人類涉足的深山或需鑽敲架繩的峭壁爬去。要爬成史無前例的第一人。但此刻我站在這難入冒險家之眼的山徑,離家不到百米,還因為出現墳墓鬆一口氣。強悍大概不是丈量我爬山的恰當詞語。
但我真氣自己沒帶登山杖。這裡無論如何都不是尋常登山步道,三五步就有橫空出世的蛛網迎面而來。輕薄壓縮褲早讓我雙腿被蚊蟲透徹叮咬幾十個奇癢腫包就算了,會干擾前行的黏人蛛網才教人惱怒。我四周尋找,截斷一根倒竹為杖,邊走邊舉杖往半空揮打,總算解除了蛛網糾纏。
這是冬季以外攀爬淺山和中級山才有的講究:
視蚊蚋蛛蛭蟲蠅為必要的存在,學習與必要存在同行,如果逃不掉,就開放接納牠們在身上留下囓咬、過敏、搔癢與瘢痕。
但不是人人接納得了你和你的身體以此形式把山帶下山。某個夏天走完宜蘭一條舊林道,雙臂布滿芒草割痕和蟲蚋叮咬的嚴重過敏,儘管如此我仍穿著短袖與友人相約到一間講究的茶坊。茶坊女主人見了我雙手,起先驚恐,然後隱隱露出嫌惡。她不解為什麼要讓身體如此不雅不潔。
她不明白爬山的人,有時沒來由會想在自己身上留下山的痕跡。登山界倡議人類當力行「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我對自己爬山的身體秘密協議「山林留痕」,任高山紫外線在臉上留斑點,任連續陡降一千公尺的下坡在大姆趾留下烏黑的指甲片,任手腳並用的路段在手腳指縫留下難以洗淨的污痕,任水蛭鑽進褲腳在腳踝留下一圈星星點點的血痕破口……
會不會是,這些身體被山刮擦過的痕跡,比高舉標牌的山頭攻頂照片更具紀念性,更契合我通過爬山想嚮往或追求的東西?
我曾和一同爬山的夥伴在南湖圈谷尋找羊背石。那是冰河來過現在海拔三千四百公尺處的證明之一。遠遠望去羊群一樣的石堆,近看表面滿是被冰河劇烈磨蝕過的痕跡。痕跡留下時間的懸念,故事有了穿孔鑿隙的空間,但要說一個以億萬年為單位的故事,對於終究對人類懷有更多情感的我來說,還是太難。
何況石頭無機。而我的身體只要還活下去,就能繼續經受山林和現實的刮擦,留下深深淺淺的痕跡。我總有故事可說。
爬山這事之所以越來越多人做,無非也寄望將心靈的某些感知和精神追求的象徵兌現或賦形吧——我攀登,我征服,我墜落,我臣服,我受苦,我超脫,我滌淨。
繞回我家後頭這座淺山吧。過了墳墓後,我依舊執迷於有條能夠上切稜線的路,沿著稜線或許能接上我常走的環大台北天際線步道。我穿越一些菜園和工寮,但總在竹林後被高大的姑婆芋和雜樹林擋住。如果有工作手套和山刀就好了。看著雖無路跡、但只差一條等高線就能上到稜線的離線地圖,要是工具齊備,或許我能開出一條獨家祕徑呢。
回程路上,菜園讓我鬆懈心志,我踏進來時未走的新路,在某個石塊與蔓草遍佈之處,聞到一陣惡臭。是屍體的味道。野生動物多的山中出現這味道並不奇怪,但我猛然想起剛搬家時讀過幾篇新聞,說的是新家周圍多山區,因此也成了某些兇殺案棄屍地點……我再無披荊斬棘的勇氣,回頭慌不擇路時,一頭撞上了橫叉樹枝,至今左額仍有一腫塊,由蚊子和樹枝一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