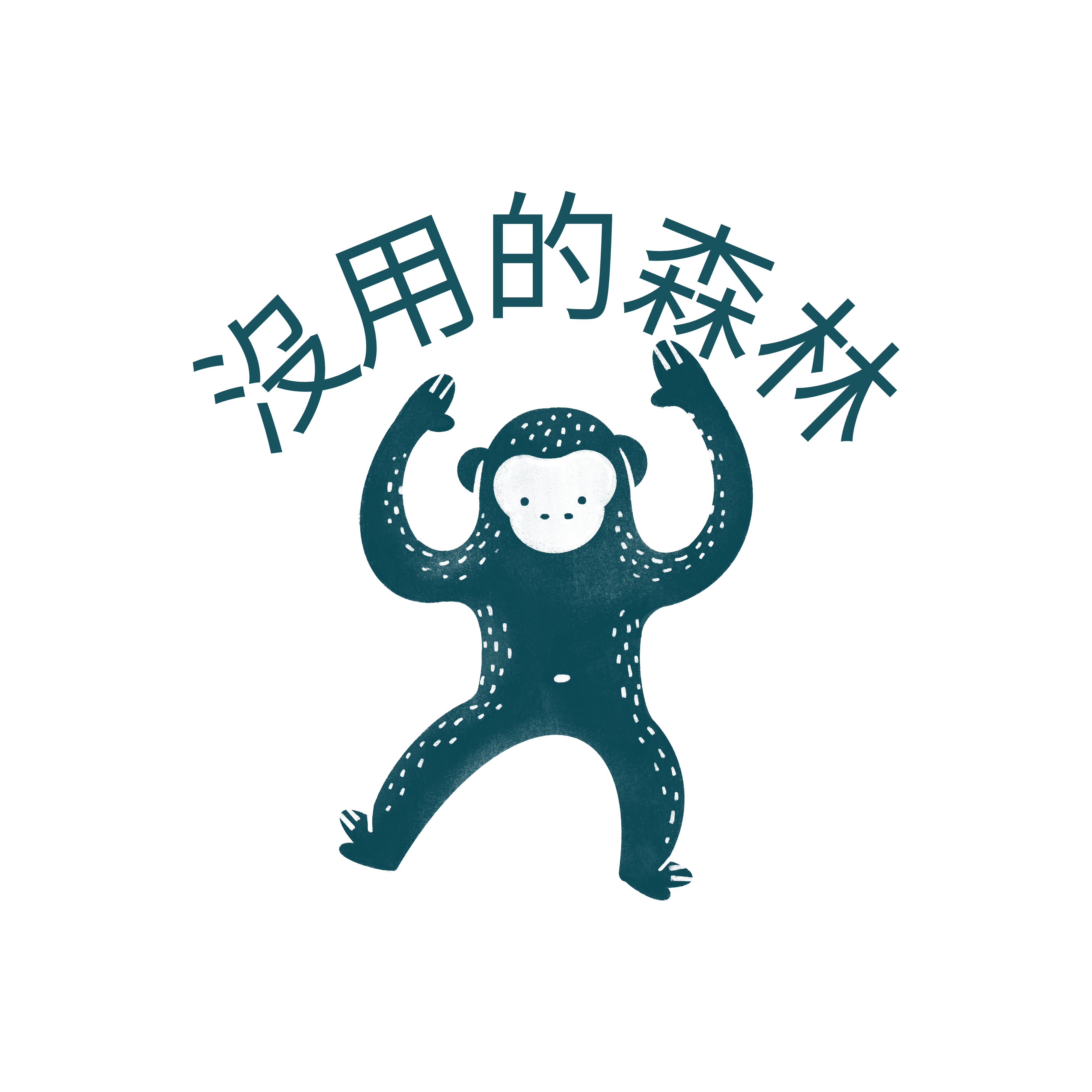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事件1
這份灌溉的愛,期限超過50年——八田與一開啟的水利大冒險
假如你的山海圳之行是從台江啟程,很難不注意到沿途除了給人通行的綠道,也有眾多宛如土地血管的「水路」,這些水路可不是一般河川溪圳,它們都是嘉南大圳的灌溉渠道。
嘉南大圳的名聲響亮,但對島嶼大多數人來說,若非近年極端氣候導致嘉南平原常傳出農田缺水的新聞,這條完工近百年的台灣重要水利工程,可能只活在歷史課本中,即便走在大圳水路旁也相看而不相識,更無法想像:這些密布在平原上的水路,長度總和達一萬六千公里,足足可繞上地球半圈。
不只長度驚人,嘉南大圳從設計、施工到後續成效等方面,都締造了許多紀錄:它的工程內容複雜,包含烏山頭水庫、烏山嶺引水道、取水、給水、排水、防潮防洪等設施;工程經費多達5千4百多萬日圓,破了當時水利工程費用;由於施工期間遇到了引水道挖鑿不順、爆炸造成60人傷亡等意外,以及日本關東大地震造成工程延宕,從1920年動工、直到1930年才全部完工。
雖然耗時10年,但大圳的灌溉總面積多達15萬公頃,也因八田與一提議「三年輪作」的灌溉法,原本因水源不足、土壤鹽份過高等因素,只能看天吃飯的農人們,能在地力上升的農田耕種出產量大幅提昇的水稻、甘蔗等作物,日本政府也成功將台灣變成了母國糧食的提供者。
更驚人的是,當年大圳設計者八田與一以特殊的「半水成填充式工法」建成的烏山頭水庫,原本評估使用年限為50年,如今服役超過快一倍時間卻依然盡責擔負儲水供水任務,這份珍貴的水利遺產,正是當年被嘲諷「狂言」的八田與一縝密擘畫、眾人傾力投入工程,以及一代代大圳工作者的經營維護所共同保守下來的。想知道人們如何守住這個屢遭質疑阻撓的工程以及更多大圳故事,往背包裡塞一本《圳流百年》或《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再上路吧!
#事件2
位居山海圳樞紐的古道,有賴這群人用身體修復它
提到登山,一般人心中浮現的印象要不是鄰近郊山的健行步道,就是3,000公尺以上的百岳攀登行程,但對某些登山愛好者來說,「古道」才是真正深入台灣山林之心的主角。
八通關古道、能高越嶺古道、浸水營古道……這些被重新考掘出的古道路線,因人們持續踏查走訪而未失去作為一條路的功能,有些古道則隨著時代變遷、更快速方便安全的道路出現而被替代,最終為蔓草和記憶掩蓋。早在日治時期就出現在地圖上的烏山越嶺古道,道路角色雖延續到救國團時期的東西口健行路線,最終也失落了形跡,直到山海圳綠道的倡議,人們記起它的存在,決定把路找出來,恢復路的形貌。
但找路和讓它能接納更多步伐踩踏,都不是容易的事。在台南社大沈介文和透抽(翁世豪)等人重新找出古道路線後,由千里步道協會接棒,在2019年協同林務局和嘉義林管處等單位,徵集了30名志工來到這個山海圳「從海入山」的樞紐路段,以人力而非工程機具修築出156公尺的手作步道。
為什麼東西口步道必須是一條手作步道?千里步道協會的副執行長徐銘謙分析,位在台南楠西、六甲區域的烏山嶺,因為氣候和地質的關係,土層平時乾燥易碎,若遇夏季強降雨又會被大量沖刷,本就不是穩固的地段,如果以傳統的步道工程思維搭建棧道、棧橋或其他看似堅固的人造設施,不只工程難度高,後續管理維護也是大問題,一旦設施兩邊土石被掏空,再堅固的建設也難敵自然變動之力。
協會說服公部門,東西口步道要順應地形變化施作,不要套用過去單一鋪面的作法;修築步道當日,志工們攀爬一大段又滑又陡的上坡路,利用現地的相思樹倒木和石頭做成維護邊坡、防止路面流失的結構——光是護坡減少沖刷,就能讓這段步道走起來更穩健、減少濕滑和踩踏的危險。
徐銘謙說,完工後許多志工都倍感激動,因為去時連站都站不穩的路,回程好走多了,「自己的路自己修」,這體驗可不是一般登山者能得到的!
事件3
平埔族群選擇題:如何把滅絕的語言重新放回我們嘴裡?
「可不可以請阿立祖教我講西拉雅語?」研究西拉雅文化十多年的臺南藝術大學博士生陳冠彰,有一天這樣問他相熟的社子社尪姨(神職人員)。
阿立祖是社子社奉祀的神靈,當部落舉行夜祭等重要活動時,祂會依附在尪姨身上與族人溝通,也會提出要求或給予指示。在夜祭拍攝到阿立祖唱頌族語的陳冠彰,想到人們總說西拉雅被漢化、沒有自己的語言啦,一個奇想浮現心中:存在千百年的阿立祖一定會講西拉雅語,何不請祂開立西拉雅語補習班,教自己說族語?
尪姨後來回覆陳冠彰:阿立祖沒反對,但祂沒有語言教學經驗,不知道怎麼教餒,不然,陳家弟子(阿立祖總這樣稱呼陳冠彰)有什麼問題,想知道什麼單字再來問我好了。
說到這陳冠彰摸摸頭,這個聽起來很kiang的提議竟然神靈也同意,但他語言天份實在太差,即使有正正經經研究西拉雅語的太太和朋友協助,還是學得li-li-lak-lak。
藝術家請神來當族語家教,這點子固然有點啼笑皆非,卻也映照了西拉雅語,以及諸如洪安雅語(Hoanya)、巴宰語(Basay)、大武壠語(Taivoan)等其他平埔族群的語言困境——究竟要怎麼把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已滅絕」的語言找回來呢?
幸而這個超級艱難、卻事關平埔族群文化延續與政治身分確認的挑戰,在不同族人的分頭努力下,踏出一步步清晰的足跡。透過荷蘭人因傳教、商業往來留下以羅馬拼音拼寫西拉雅等族語的契約文書(如「新港文書」、「馬太福音」等),以及日本學者淺井惠倫、馬淵東一等人紀錄的歌謠錄音等文物,各平埔族群與學者共同合作,逐步復振了被視為死亡的語言。
然而,政府雖投入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卻僅有資金挹注,其他具體的復振行動仍須族人自立自強。長期關注西拉雅社群的陳冠彰說,要原本偏鄉、少子的部落族群維持學習族語的動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看到頭社、社子等部落族人,願意年復一年投入祭典的舉辦、學習牽曲等祭儀,甚至許多族人選擇讓孩子不是去補習班學習更有競爭力的英語,而是回祭典從歌謠中學習族語,「願意選擇這樣的價值觀,我覺得是比冒險更艱苦、更有勇氣的事」。
※本文為受「橘子關懷基金會」2020年「夏日學園:一起向山致敬|山海圳,挑戰從零開始」活動委託,於活動期間隨行記錄,並於活動結束後前往山海圳路線進行資料蒐集與相關採訪後發表之 「冒險解禁」線上展覽 撰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