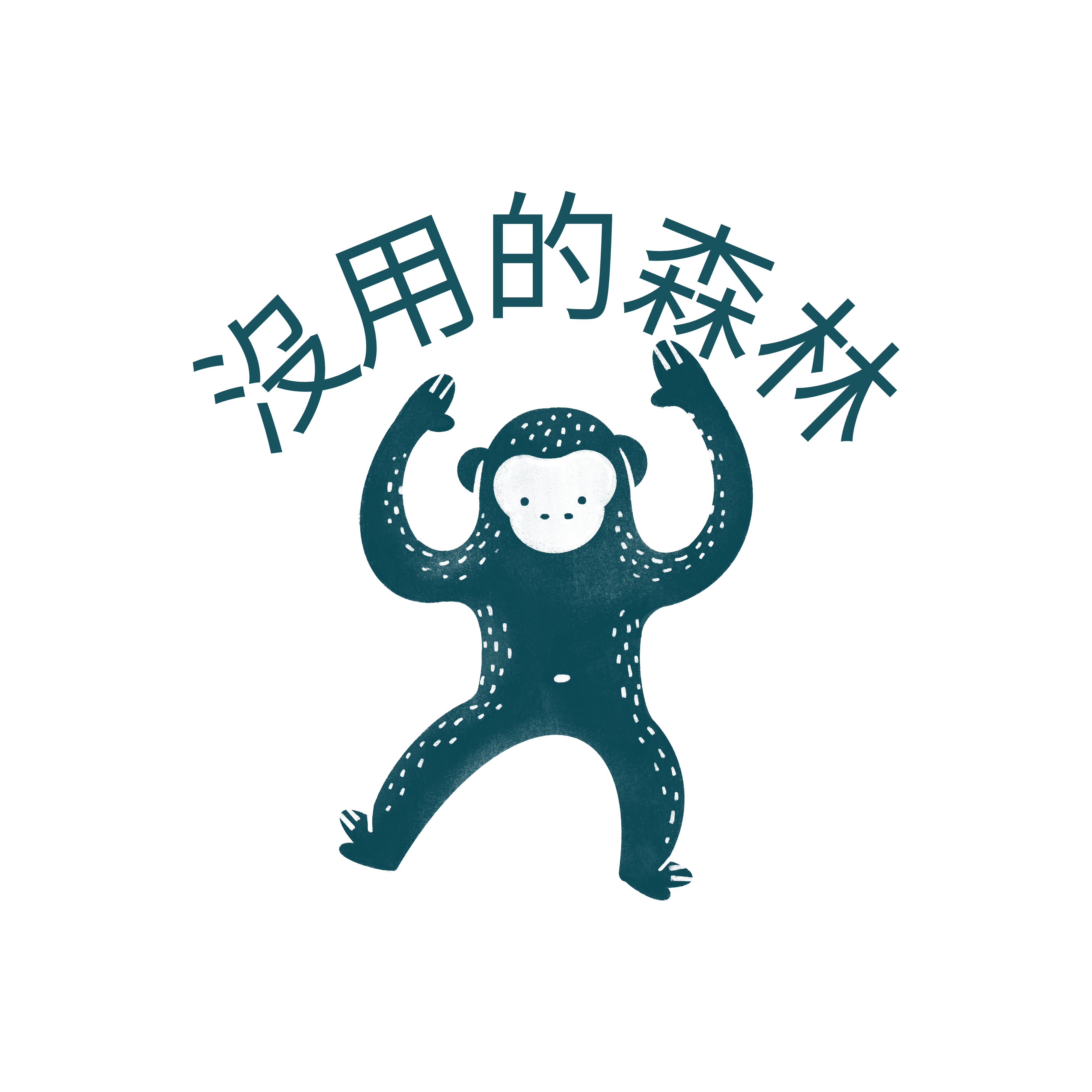二○一一年,史蒂夫.賈柏斯過世兩天,台灣小說家與時事評論者楊 …
標籤:
舞蹈
-
-
1997年,原舞者在臺北會議中心演舉行一場公演,舞臺上,來自 …
-
我被表演藝術戴上了一副脫不掉的眼鏡,於是某個部落青年和我站在 …
-
文字可以使勁索討落實,但只能要到局部。你記錄得了線條、速度、 …
-
到最後,人們已然無法區別,造成自己孤絕的究竟是外在環境、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