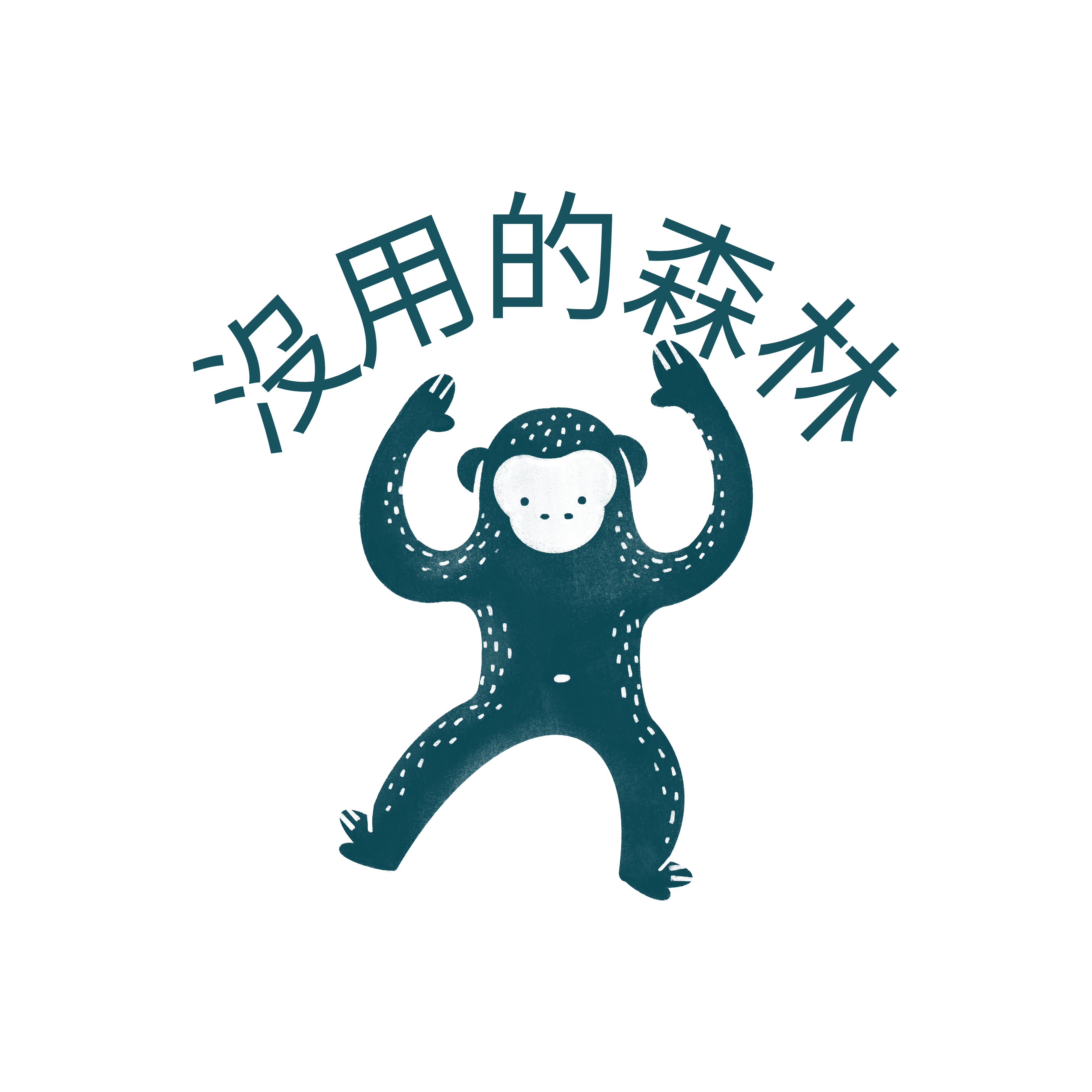「要怎麼樣才能把我看到的畫面也讓你看到?」陳德鴻出聲問。
當時,我們已瀏覽了「萬里溼地植物庇護中心」自園區入口開始好幾個生態池——這池是台灣水韭、那池是水車前,還有一度野外滅絕、現在成功復育的台灣萍蓬草……陳德鴻沿著逐個水盆和池子介紹,內容或許和他平日接待不同團體的導覽流程差不多,然而,聆聽他說話的我並不在現場,而是間隔兩個螢幕的距離,更具體地說,是與萬里相隔數十公里的遠距。
身為採訪者,這是我頭一次面臨「遠端遙控受訪者行動」的奇特經歷。每當陳德鴻移往另一個種植不同水生植物的生態池,我們總要重複一次這樣的對話:
「這樣看得到嗎?我看不到畫面,要怎麼調整你告訴我。」
「老師你的手機再往下一點……往右……有了,我看到了!你剛才說這是?」
這是台灣水韭。那是水車前。水鱉。台灣萍蓬草。穗花棋盤腳。分株假紫萁。長葉茅膏菜。小毛氈苔。黃花狸藻。絲葉狸藻。芡實。小果菱……儘管每一株水生植物都被攝入陳德鴻的手機鏡頭,不必俯身低就水面而是改由這些水生植物逼近我,但鏡頭下的特寫有時難免失焦模糊,必須仰賴放在電腦旁的水生植物圖鑑,供我即時查閱這些體型多半渺小的水中植物,到底有著怎樣的型態和構造。
園子裡,幾乎遍處都是的風箱樹正在盛放花期,陳德鴻每遇一棵開花的樹,必定停下腳步,將鏡頭對著整樹炸開的一球球白色煙火,「風箱樹開花很漂亮吧!我希望你看看這麼漂亮的畫面」,鏡頭外的他想必深吸了一口氣,「這裡很香喔,風箱樹的花很香,不野,是優雅的清香……」
可惜,鏡頭無從傳遞這股不野的香氣,也沒有任何一本圖鑑能提供植物嗅聞起來的感覺。
逾1/3物種瀕危的現實
曾經假想過:在並不遙遠的未來,人類也許得憑藉肉眼親睹之外的形式,才能與眾多的台灣水生植物重新相遇。
2019年深秋,我前往宜蘭的福山植物園採訪林試所在全台各植物園如火如荼展開的瀕危植物移地復育計畫,當時,福山植物園的研究員林建融提到,只要是野外瀕危絕種的稀有植物,上山下海哪怕墳場他都願意去尋,唯獨水生植物,他一度非常抗拒尋找蹤跡,「因為收集過程的心理打擊很大……消失速度實在太快,可能你才知道一個新的棲地,結果去的時候它已經徹底消失了」。
根據不同時期的台灣學者研究,台灣原生的水生植物約有300多個分類群,多樣性堪稱豐富。這些水生植物顧名思義生長在水域中,從湖泊、埤塘、溪流、溝渠、河沼、溼地、潮間帶……都有它們出沒的形跡。只是,台灣的水域環境並不穩定,除了地理環境和氣候變遷造成越來越長的乾旱季節,農業衰退和土地開發等人為因素更造成水域環境的遽變,100多種水生植物因此成為瀕危甚至滅絕物種,也就是說,台灣有三分之一的水生植物正面臨生存危機。其中,9種台灣特有種的水生植物——臺灣水韭、水社柳和水柳、臺灣萍蓬草、臺灣水龍、大安水蓑衣、臺灣水蕹、龍潭莕菜和桃園草,都曾遭遇棲地消失的絕境,也讓族群本就稀少的植物住民置身於「種族滅絕」的恐怖現實中。
然而,對大部分生活在台灣的人而言,水域本就不是日常熟悉、互動頻繁的環境,水生植物在棲地中的形態和生命歷程也往往陌生,真要說起來,荷花、睡蓮、菱角,還有近年躍居盤中佳餚的野蓮(學名為「龍骨瓣莕菜」),大概是人們較熟悉的水生植物;而另一道經典炒青菜選擇——空心菜,其實也是水裡的住民。
至於那些消失殆盡的水生植物,到底該如何想像它們在原棲地自然生長的模樣?深入福山植物園的僻靜角落,林建融撥開人高叢草,露出一面下雨過後自然形成的透澈水沼,裡頭盡是一種紅皮書標示為「野外滅絕」的水生植物,桃園石龍尾。植株全部沉在水中的它們,隨著波紋款擺鮮嫩莖葉,構成一幅美麗的動態畫面。
想到並不很久以前,台灣隨處可見的埤塘水池裡盡是這樣的景致,眼前那過分鮮綠到幾乎不真實的桃園石龍尾,教我不由想起了博物館裡戴上VR裝置就可看見栩栩如生的史前生物,例如恐龍。從那時起,我經常懷疑,會不會有一天,我們同樣得透過科技而非肉眼,才能看見原本棲住在這片土地的水生植物?
水域:孕育多樣性也蘊藏記憶
沒想到是一場席捲全球的疫情加速想像成為真實。
原本預定趁著許多水生植物開花的初夏拜訪隸屬於荒野保護協會的「萬里溼地植物庇護中心」,北台灣的新冠肺炎疫情隨即白熱化,我們只得取消親臨現場,委請長年擔任庇護中心主持人的陳德鴻以視訊形式帶我線上瀏覽園中植物。
雖然無從將身體投入現場,用眼耳鼻舌身意感知水生植物鮮活的生命,以及構成庇護條件的當地氣候、地形、水、風、土壤等環境,但從拿著手機權充鏡頭一個多小時,不時提醒我注意畫面中植物的細微特殊構造,偶爾飛來一兩句:「你有聽見拉都希氏赤蛙的叫聲嗎?」、「有看到蓋斑鬥魚從萍蓬草旁邊游過去?」可以感覺到,陳德鴻投注在園區生態的熱情和對所有寓居物種的理解,是這片土地發揮庇護功能的關鍵。
2003年,萬里溼地植物庇護中心正式成立,在此之前,這裡是陳德鴻老家的水梯田。長輩年邁、田地廢耕,這片水田本該走向灌木和芒草進駐的陸化宿命,誰知道陳德鴻40歲人生一個大轉彎,栽進了植物保育的世界,家族蕪田的命運也隨之扭轉,成了接納全台瀕危水生植物的民間重要據點。
接觸植物保育之前,陳德鴻從事陶藝工作,笑稱自己也曾是唯利是圖的生意人,後來陶瓷產業式微,正值中年的他也不戀棧,離開工作跑道後,憑著一股如今想來衝動的激情,扎進了生態保育的浪潮。從棲蘭山檜木保育、搶救雙連埤溼地、夢幻湖台灣水韭復育……他無役不與,最後乾脆把棲地大肆破壞後無處可去的植物都帶回老家田地,就著梯田闢出人工生態池、垂直岩壁、泥炭苔溼地等不同的微棲地,供生長條件需求不同的物種們各安其所。
為什麼偏偏對水生植物情有獨鍾?陳德鴻不諱言,起初也被「美」吸引,無論沉水、浮水或是挺出水面,許多水生植物都有一副纖秀可人的形象。他墜入情網的第一株植物,是如今野外同樣難見的野菱。這種台灣原生的菱科植物,浮水葉片造型特殊、排列有序、結構井然,小巧的果實也漂亮,陳德鴻形容它不只好看,更是懂得有效吸收光照的數學高手。
不光是植物,孕育它們的水域,也蓄養著陳德鴻重要的情感記憶。「只要跟水有關連的環境,我都特別喜歡……有水的地方,我的心情會更寧靜」,他也經常被水澤召回無憂無慮的童年,跟大人一起下田,圖的是農忙一天有五餐可吃,勞動弄髒了身體,更是去溪邊戲水的好藉口。60多歲的他笑說,這些年他天天往萬里跑,只要進園子裡,哪怕拔一整天的草也不會厭倦,「這樣講好像有點逃避,但至少在這裡我可以優遊自在做我想做的」,何況疫情嚴峻,「我一個人躲在這裡還不用戴口罩,多爽快,多療癒!」說罷哈哈大笑。
擁有藝術背景,初始也被水域生態的美吸引,陳德鴻運用所長,將庇護中心的各角落微棲地布置得既符合植物生長需求,又有園藝造景的視覺美感:一片垂直岩壁,上方砌出一窪水槽,使活水源源不絕流注岩壁,形成一面垂直溼地,油點草、穗花斑葉蘭,野慈菇等植物依壁而生;生態池旁的泥炭苔地上豎起幾根拾來的枯木,就成了分株假紫萁的棲地。「重點是對植物熟悉,就有辦法搭配出一個畫面」,然而,生態造景又與藝術造型不同,「植物是不可控的,你要能接受,有的時候它就是會消失,不要違逆它,但很自然,明年它又會再來」。
雖然在乎美感,但他也痛心於許多人雖愛水生植物的美,卻忽略從生態角度認識這個脆弱的族群,「很多人造水池,結果種的是布袋蓮、水芙蓉這些強勢外來種,雖然漂亮,但沒有融入保育觀念,非常可惜」。
這令我想起了林建融在福山植物園後,曾領我去雙連埤一處菜園旁的溝渠,清澈的水流中有一小簇他懷疑可能是野生的桃園石龍尾。在石龍尾周圍,有一大片水生植物同樣引起我的讚嘆,但林建融淡淡說道:「那是外來的粉綠狐尾藻」,最早因姣好外型被水族業者引進,流到野外環境後卻大肆生長,益發壓迫原本緊縮的原生物種生存空間。
屆時,這小簇或許是野外原生的桃園石龍尾,恐怕也難再棲存。
貼近邊界、微觀以對的精采世界
當我們談論人類與植物共生,滿足美感需求和維護生態平衡是否只能非此即彼?
對於工作力求同時呈現兩者的科學繪圖師來說,這一題當然不是二選一。近年隨著各類環境議題重啟、人對自然的渴求轉趨強烈,以繪製生物型態和生態樣貌為主的科學繪畫跳出了原本服務學術研究的框架,獲得大眾矚目。通過繪畫的表現,人們看見的自然,如何迥異於照片和影像捕捉的形象?
從「生物多樣性」出發的全景呈現,就是繪畫能做到的第一個「看見奇蹟」。2016年,由林務局委託、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承辦的「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為了呈現貢寮水梯田行友善農法後在維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成果,邀請生態插畫家黃瀚嶢繪製了一幅「和禾水梯田」插畫摺頁。畫面呈現了水梯田「從上游到下游的地景關連與生態」、「四季和禾農法」以及「自然賜予的生物多樣性惠益」三個主題,其中一層地景,黃瀚嶢繪製了夏末秋初稻子剛收割後的水田,畫面中,除了割剩的稻頭在遠景暗示著時間流動,前景和中景充滿了數十種生物,全是稻作收割後迫不及待竄出來開花結果或交配繁殖的植物、昆蟲與覓食而來的動物。
「從研究的角度來說,水生植物很冷門,又容易消失,所以關於水生植物,我也就畫過這麼一個案子」,黃瀚嶢說,而這幅生態插圖中的水域溼地,也跟一般人想像的荒野不同,是與人類生活緊密關連的農業環境。
「水田是有生產力的溼地」,森林研究所畢業、目前身兼插畫家與社大自然課程講師的黃瀚嶢解釋,溼地是個很廣泛的詞,開闊的靜水域造就了獨特生態,以水生植物來說,有些挺水植物相對高大,但多數水生植物都很小,有些甚至生長在水域邊緣處,水退去才能看到,水漲起它就消失,不管是看溼地或水生植物的靜水域,唯有貼近邊界,以微觀視角注視,才能看見這個細微卻精采的世界。
他以自己繪製的和禾水梯田為例,雖然只是一池稻作收成後的水面,卻由許多微地景構成,「這些微小結構會影響很多生物的選擇」,因此,比起一般繪畫,生態插畫在構圖上更須尊重生物本身,從它們的外型、對棲地的偏好、和棲地其他物種的關係……都必須納入考量,「生態插畫必須傳達一個生態學的敘事」,黃瀚嶢說,因此他必須知曉:葦草蘭偏好生長在水田邊坡,蜘蛛捕獵會站在水面上,而食蟹獴會在頁岩上大快朵頤福壽螺……
但這並不表示面對科學知識,創作者的藝術詮釋和巧思只得退位或隱遁,「比如說,你怎麼用某種植物創造動物停棲的位置,讓動物和植物間發生對話,或是讓食蟹獴回頭帶出視覺的引導,這些故事就是我可以創造的地方」。
「水生植物是個滿強調生態的主題」,黃瀚嶢說,除了它們多半嬌小,棲地變動性大容易消失,更因為水域是個高度生物多樣性的環境,昆蟲、浮游生物和植物在此緊密共生,形成食物鏈,而這樣的環境若位在低海拔也經常和人類生活相連,「大部分的溼地如河口、湖泊、埤塘,跟人類聚落都很近,甚至跟產業綁在一起,桃園埤塘就是農業蓄水池,當農業消失,埤塘就跟著消失」,黃瀚嶢說,因為繪製貢寮水梯田的案子,也促使他不斷思考:當擾動和共生成為必然,人類到底該把自己置於哪個棲位、扮演何種角色?
到不了的地方 失落的體驗
在黃瀚嶢的指引下,我循著網路找到了另一個無法前往現場而能看見水生植物的地方。
那是一幅畫。場景是台北,一個可遙望陽明山系的向天山和大屯山稜線之處,正中一大片水澤。時序入秋,幾株台灣欒樹在左岸猛然綻放滿樹黃花,右岸近處一些穗花旗盤腳低調開著遲來的花。水澤裡滿滿的植物:挺水婀娜的藍睡蓮底下,是往畫面深處蔓延開展的一大片石龍尾,葦草蘭盛花群聚的後方,一隻水獺凝視著遠方亂蹄踏破幽靜氛圍的梅花鹿群。水鳥驚飛。幾乎不可見的遠方,彷彿一艘舟影逐鹿而來。
這是無論疫情與否,我們都無從去到的現場——六百年前的古台北湖,由台灣的生態繪畫家陳一銘所繪。憑藉長年扎實的野外調查與科學繪圖經驗,以及還原不可見之處的想像力與靈光,陳一銘畫出了隱沒在歷史之前的〈蠻湮台北〉,把已被逐出台北盆地生態版圖的物種,重新迎回它們曾經共生的棲地。
通過數位科技裝置和繪畫,最終得見了無法眼見的水生花們,然而失落了肉眼和肉身與它們相遇的經驗,對人類或文明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台灣萍蓬草的搶救紀事
在陳德鴻一手打造的萬里溼地庇護中心,原本高高低低的梯田,被改造為一個個大小不等的生態池,每個生態池都有保育的主角:野菱、蓴菜、水韭、水鱉……而台灣萍蓬草(Nuphar Shimadai Hyata)顯然是箇中領頭,連續幾個池子都可見到昂揚於水面、綻放中的鮮豔黃花。
談到溼地水生植物的保育經過,台灣萍蓬草可能是其中曝光度最高的物種,除了具有「台灣特有種」的身分外,也因台灣原生的四種睡蓮科植物中,睡蓮與藍睡蓮早已消失於野外,僅萍蓬草和芡實還偶見於自然環境。原本分布於桃園新竹一帶的埤塘和池沼,隨著農業用地減少、土地開發轉為他用,萍蓬草和其他水生植物的棲地迅速消失,90年代起便開始有民間和政府部門投入資源協助原棲地保存和萍蓬草移地保育。30年來,台灣萍蓬草已偶爾能在公園、校園等人工生態池看到,但由於它的種子散佈能力有限、生長區域裡又多競爭對象,只能靠無性生殖擴大族群數量。即使是明星保育物種,萍蓬草猶須仰賴人類傾力襄助才能維繫繁衍,其他列名瀕危卻更不起眼的水生植物族群如石龍尾、龍潭莕菜、田蔥、挖耳草等,只能翹首企盼更多人類的慧眼和關愛了。
(本文首刊於《經典雜誌》第278期,2021年9月)